-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第1版 (2016年1月1日)
- 外文书名: Foragers, Farmers, and Fossil Fuels: How Human Values Evolve
- 丛书名: 历史的镜像
- 精装: 328页
- 语种: 简体中文
- 开本: 16
- ISBN: 9787508657097
- 条形码: 9787508657097
- 商品尺寸: 23.6 x 17.6 x 2.4 cm
- 商品重量: 680 g
- 品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Details
基本信息
编辑推荐
《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全球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西方将主宰多久》作者最新力作;从史前人类,到现代社会,在数万年历史中找寻社会演变的本质,揭示物质力量与人类文明的根本关系
名人推荐
莫里斯的这本新书是富有意义的。这种努力是非常可贵的。他的观点也为现代人理解乃至宽容过去时代的价值观,至少是比较平心静气对待它们,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基础。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人类的价值观念与生产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这个道理经常被忘记,也就需要学者经常用细致的研究来重新确认。在淘汰化石能源的时代,莫里斯从人类能源的变迁阐述人类重要价值观的变迁,很有新意,也会给读者带来对当代经济与政治生活的启迪。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媒体推荐
在这部引人入胜的作品中,伊恩•莫里斯带领读者从史前人类跨越到现代社会,提出了一种文化新理论,将其与经济因素以及人类从自然中获得能量和资源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新颖大胆、才华横溢而又激动人心。
——达龙•阿西莫格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拉克奖得主
你可能不会完全赞同《人类的演变》中的所有观点,但是一定会非常享受阅读这部发人深省的杰作。更为重要的是,伊恩•莫里斯在书中提出的大胆而清晰的假设,对尚处于萌芽期的科学史学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科学》杂志
《人类的演变》对伦理价值的演变与分歧给出了令人激动的解释……在伊恩•莫里斯这位才华横溢的写作者与思想家笔下,文字化成了一次迷人而充满智慧的旅程。
——《科克斯评论》
作者简介
伊恩•莫里斯,全球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中信出版集团2014年度致敬作者。已出版《西方将主宰多久》《文明的度量》《战争》等多部著作,得到学术界和读者的一致好评。其中《西方将主宰多久》荣获《纽约时报》年度杰出图书、《经济学人》年度图书、国际笔会/福克纳奖图书、“益得书摘”国际图书奖、英国奥威尔图书奖(入围)、FT中文网年度荐书等,入选首期“解放书单”;《文明的度量》入选“中国大众好书榜”等。
目录
推荐序 价值观缘何而来?
导论
正篇
第一章 每个时代都是得其所需
乔治先生的故事
三种社会体系
历史的诠释与理解
一些“歪论”
历史学家的错误
第二章 采集者时代
什么是采集者?
等公交的马赛人猎手
采集者的生存方式
昆申人的“大酋长”与肖松尼人的“兔老大”
第三章 农耕时代
什么是农耕者?
普通农民的生活记录
农耕时代的生存方式以及希腊奇迹
阿格拉利亚世界
重返阿西罗斯
第四章 工业时代
什么是化石燃料群体?
信息充足的时代
从阿格拉利亚到因达斯特里亚
科学的发展与更自由的世界
阿斯罗斯之后:塔利班枪击事件
第五章 人类的演变:生物、文化与未来
红皇后效应
“漫长的夏天”与幸运纬度带
海洋城邦与科技革命
三个问题的答案
评论篇
第六章 机器人和高级人工智能的时代会更美好吗?
第七章 思想的局限
第八章 价值观中的永恒、发展与自我
第九章 灯火阑珊处:文明崩溃之后
回应篇
第十章 我对一切事物的正见
我的回应
两个假设
三个阶段,三种社会形态
能量来源与人类价值观
乔治先生犯错了吗?
21世纪的演变核心
序言
价值观缘何而来?
何怀宏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莫里斯的新书《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是以他2012年末在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观研究中心的坦纳讲座的演讲,以及4位评论人的评论和他的回应为基础结集而成的。此书所围绕的是莫里斯提出的一个中心观点,即他认为在人类过去两万年的历史中,人类的价值观经历了三个大致交替出现的体系。与每一种价值观相关联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而每一种组织形式又是由人类从周遭世界获取能量的特定方式决定的。
这三个价值体系就是书名用押头韵——采集者/觅食者(foragers)、农夫/农耕者(farmers)和化石燃料使用者 (fossil fuels)——所示的价值观体系,它们其实也可以说就是对应于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三种不同的价值观体系——莫里斯有时借用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 的说法把农业社会称为“阿格拉里亚”(Agraria),把工业社会称为“因达斯特里亚”(Industria)。
莫里斯认为,第一种“觅食价值观”的价值体系,因为与它相关的社会主要通过采集野生植物和狩猎野生动物来维生,是很小规模的群体且流动性很大,故而觅食者倾向于看重平等,也比较能够容忍暴力。不过他认为19世纪有关觅食者实行“原始共产主义”,所有物资全部归公的观念是错误的。第二种是 “农业价值观”的体系,因为与它相关的社会主要靠经过驯化的动植物来维持生计,农耕者倾向于更看重等级制度而非平等,比较不能容忍暴力。所以往往建立大的等级社会的国家以保障定居者和平地休养生息。第三种是“化石燃料价值观”的体系,它所关联的社会主要通过钻取已经转变为煤、气和油的植物化石能量来增加现存动植物的能量,故而化石燃料使用者倾向于看重大多数类型的平等而非等级制度,且非常不能容忍暴力。
价值观念众多且纷纭复杂,莫里斯说他只能在价值观的诸多因素中选取了两个他认为特别重要的因素,即对待平等与暴力的态度,主要以这两点来标示三种不同价值观的差异。他不回避他的观点可能遇到的批评和定性,诸如简化论、本质论、唯物论、实用主义等,甚至坦承自己就是这样的观点,而只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这样的观点并不是不正确的,或者至少说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任何学者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某种程度上的本质论和简化论。
这的确使熟悉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人们很容易想起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欧内斯特•盖尔纳,见第75页注释①。——编者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观点,但这里是某种生产力——觅取能量的方式——直接决定价值观念,他自然也不会引出阶级斗争的观点,更勿论无产阶级专政。相反,他是相当赞成今天发达的“化石燃料使用者社会”的主流思想的,赞成社会合作与自由市场,或者如书中一个评论者理查德•西福德(Richard Seaford)所说,是赞成一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但更确切地说,他是赞成一种“与时俱进”、因需而变的价值观。如果他生活在过去的社会,他也会接受过去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这倒也是为现代人比较平心静气地看待、理解和同情地解释过去的价值观开辟了一条道路。他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背后的哲学是一种功利主义或效益主义,这也可以为同情地理解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预防少数人的浪漫政治思想逾越界限而伤至社会提供一个恰当的基础。
莫里斯的观点简单明快,而且的确抓住了一个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人必须获得物质能量才能生存下去,而且获得的能量较多才能繁荣,才能发展起一套精致甚至奢华的文化。而且,他对未来虽然也有展望,但没有一套乌托邦的社会理想,未来是开放的,有几种可能,包括由碳基生物变为硅基生物的可能,也有核战争的可能。
莫里斯的“价值观三段论”既有一种简化的锋利性,又包含着许多生命的常识,这些常识是拒斥书斋里产生的“意识形态”的。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人类的价值观的形成是相当复杂的,即便承认人们获取能量的方式与他们的价值观念之间有某种最初的决定关系,在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许多中介的,比如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它们可能对人们的价值观的形成有更直接的作用,还有价值观念和其他观念本身的相互作用,包括这些观念对获取能量方式的反作用,等等。比如说,有时价值观对一个社会的物质能量获取方式甚至能起一种定向的作用,有些文明社会(比如经济一度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明清时代的社会)迟迟未进入一种发达的市场和工业社会,正是上层主流价值追求的“志不在此”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最长远的观点和最根本的因素来看,莫里斯的观点也许能够解释某些根本的共性:人只有吃饭才能生存,只有有丰富的多余产品才能发展。但不容易解释一代代活着的人所面对的生存和社会环境的多样性,而活着的人要对付的却主要是自己的特殊性,那些共性由于太一般甚至是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的。
另一个问题则是涉及价值观念的恒久性,在变化的价值观念中有没有一些不变的核心价值,莫里斯的确提到了几种,比如“待人公平,行事公正,爱憎分明,防患未然,敬畏神明”等。但他倾向于认为这是人类生物演化的结果,乃至是人和动物共有的。当然,人类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是人同时也进行着文化演化,但他还是坚持我们关于何为正直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我们如何从周遭世界获取能量。在每一个阶段,能量获取的模式都决定了人口规模和密度,这些又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社会组织形态的效果最佳,继而又使得某些价值观体系相对更成功、更受欢迎。每一个时代的观念其实都是“得其所需”。
莫里斯的分析数据常常是饶有趣味、引人入胜的。他谈到觅食者并未刻意改变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而农耕者由于其最重要的能量来源是已经驯化的动植物,他们就刻意改变了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在觅食社会,每平方英里 土地通常只需支撑不到一人的生存,如果环境恶劣,这一比例可能会降低到每十平方英里养活一个人。但是,农业社会的人口密度往往会超过每平方英里10人。道德体系要满足能量获取的要求,而对于能量获取介于10 000~30 000千卡/人/天之间的(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要求之一便是接受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觅食者的暴力死亡率超过10%,而农耕者的这一比率接近5%,有时还要低得多。农耕者只有在等级森严、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和平的世界里才能
幸存,他们因此而重视等级与和平。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西方经济体,人均能量获取增长了7倍,从1800年前后的约38 000千卡/人/天,大增到20世纪70年代的230 000千卡/人/天。如今,全球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45人,也就是说世界上宜居部分的人口密度高达100人/平方公里。而农业社会的典型人口密度30多人/平方公里,2000年,人类的身高平均比1900年他们的曾祖父母高10厘米,寿命长了30年,扣除物价因素后的收入高出了5倍。
莫里斯还谈到通向现代“工业社会”两条路径:自由路径和非自由路径。在有些年代,比如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非自由路径看起来比自由路径的速度更快,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重塑的非自由发展同样也造就了比自由版本更快的经济成长——尽管这里有起点较低的原因,且同时引发了环境灾害的负面外部效应及大规模腐败。他认为归根结底还是自由路径更为成功,因为它不仅在创造财富和自由方面,还在减少暴力乃至提升平等方面都占有优势。
和《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观点有些不同,在莫里斯看来,从2002年以来,不管以任何方式来衡量,全球基尼系数都是下降的。虽然数据略有不同,但他和《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的作者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观点却是一致的,即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在减少暴力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1900~2000年死于暴力人数为1亿~2亿,仅占那段时期在世上生活的100亿人的1%~2%。使用化石燃料的20世纪比觅食采集者的世界要安全10倍,比农耕者的世界也要安全2~3倍。自1989年以来,战争(国际战争和内战)的数量直线下跌,全世界95%的核弹头已被销毁,暴力犯罪率暴跌,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的暴力致死率已经下降到区区0.7%。
也就是说,伴随着三个阶段的人们对暴力态度的价值观的变化:即从觅食采集者的比较能容忍暴力,到农耕者的相当不能容忍暴力,再到化石燃料使用者的非常不能容忍暴力,这三个阶段的变化是一段比较平滑的曲线;而平等的情况则有起伏,是从觅食采集者的相当平等,到农耕者的比较能接受不平等,再到化石燃料使用者的非常要求平等。在觅食者时代,平等只是存在于小范围的群体里面。到了农业社会,在已经取得了相当发展,但还不是那么发达的生产力的条件下,要支撑起一个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很难不采取一种容有等级差别的制度;但人类进展到工业社会,范围达到趋于全球化,则又是相当平等的了,即便国与国之间还不一样,但还是有人权平等的普遍要求。莫里斯认为,化石燃料人群生活在规模更大、密度更高的社群中,他们往往认为政治和性别等级都很邪恶,暴力简直就是罪恶,但他们对财富等级的容忍度一般高于觅食采集者但低于农耕者。然而,莫里斯虽从能量获取者在不同阶段的社会组织规模、流动性等方面对能量获取方式如何决定这些不同的价值做出了说明,但所提供的因果证据的确还不是很充分。他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体系中是否还存在着与动物有本质差别的人之为人的特性成分,是否还存在着一些不变的、非物质需求所能决定的成分的观点也还是可以质疑的。
所以,我以为,在对其观点进行评论的三位著名学者: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古希腊文学教授西福德、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克里斯蒂娜•M•科尔斯戈德(Christine M. Korsgaard)、耶鲁大学历史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和一位文学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评论中,科尔斯戈德的评论还是最富于挑战性的。她提出了一种真实道德价值观与成文价值观之间的差别,说这可以看作永恒的价值观与事实上只有特定时空的人们支持的价值观之间的差别。莫里斯的观点之所以会引发成文价值观和真实道德价值观之间关系的问题,原因之一是,他认为成文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生物演化造就的,这就引发了真实道德价值观是否也是如此造就的问题。如果想要让成文价值观能够支持不同的能量获取方式所必需的各种社会组织形式,人们必须认定他们的成文价值观就是真实的道德价值观,即他们必须信服,乃至信仰其价值观的正当性和真理性,乃至某种永恒不变性,他们才会有效地履行这一价值观。而价值判断能力在本质上与我们规范性或评价性地看待自我的能力相关,而这种自我评价的能力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这种规范性地看待自我的能力可能就是我们能够进行价值判断的根源,虽然它也同样可能被“意识形态”扭曲,引发一整套独属于人类的弊病和错误观念。因此,科尔斯戈德不认为人们的价值观是由人们的能量获取方式塑造的,而是人类的价值判断能力天然地倾向于依附真实道德价值观,只不过这种倾向非常脆弱,极易受到扭曲。或许我们应该认为,随着农业时代的来临,人类开始可以积聚权力和财产,各种意识形态也开始产生,它们扭曲了真实道德价值观——直到现在,人类已经进入科学和普及教育的时代,我们才开始慢慢克服这种扭曲。
莫里斯的回应是:他说他不赞同科尔斯戈德所说的“其他动物不具备规范性地看待自我的能力”的观点,也不相信有任何真实道德价值观存在。他认为现代人类代表了一个谱系的一端,而不是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所有动物,科尔斯戈德断言平等主义与和平主义是人类的缺省设置,是有些过头的本质先于存在论。人类价值观的确只能由人类所持有,但如果人类无法从环境中获取能量,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持有任何价值观,即如诗人奥登 (Auden)所说“先填饱肚子,再谈论道德”。就算是经过最无懈可击的推理所得出的脱离任何背景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真实道德价值观,也必须以某种形式的能量获取为前提。真实人类的价值观其实就是成文价值观,从头到尾,我们讨论的都是成文价值观,而成文价值观就是由我们从世界获取能量的方式所塑造。
因此,莫里斯说,他怀疑大多数人在面对出生在农业世界而非化石燃料世界这种可能性时,或许不会选择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谨慎指点的平等主义方向。最佳选择或许是更有保留的承诺秉持一整套更粗糙,也更易操作的价值观,那自然是经过生物演化的核心价值观,包括公平、爱、同情,等等。但是,要让不同时代的人们自己来决定如何对这些价值观进行最佳解读才能远离饥饿和暴力。所以,永恒价值观根本就不存在。要进入的世界是中世纪,那么秉持封建等级观念的人们会兴旺昌盛,而平等主义者则不会。今天的人们不会赞同封建观念,但与其说是这些观念不正确,不如说这些观念过时了,或者说它们只是在“过时”了的意义上是“不正确的”。
在我看来,莫里斯的回应虽然有他一向直率和坦诚的特点,但在表达和论证上还是过于强势和绝对了。他可能还是过于低估了人与动物的差别性,以及价值观念的复杂性和精神性,也没有看到人的价值观念自有其独立于物质需求和功利效用的意义。而即便价值观要充分有效地履行,也必须要有人们对它的信,即信其为真,乃至信其为普遍和永恒的真。虽然这信并不能保证价值观的内容就一定是真,但在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规范中一定还是有其客观普遍的真的——比如说无论如何都应该尊重生命,不杀害无辜。我想对这一基本价值的普遍性莫里斯估计也不会反对。他对获取物质能量方式的重视,对反对暴力的肯定,就表明实际他还是肯定了在“均富”之先的保存生命的普遍道德原则,所以,他似乎没有必要否定平等,即便在比工业社会更早的时代里平等更多的是体现为平等的生存权利而非平等的财富权利;也没有必要否定存在着真实乃至永恒的基本价值——保存生命。在这一基本点上,莫里斯和他的批评者其实是可以达成一致的。
无论如何,莫里斯的这本新书是富有意义的。莫里斯努力在最低的和最高的,最物质的和最精神的,最基本的和最高超的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虽然将其处理为一种直接的决定性联系肯定会有不少问题,但这种努力是非常可贵的。而且,这也是在高超理论与意识形态面前捍卫基本常识,有助于防止那种过于强调精神力量的、浪漫的唯意志论在变成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之后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他的观点也为现代人理解乃至宽容过去时代的价值观,至少是比较平心静气对待它们,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基础。
文摘
1982年,我去希腊进行平生第一次考古发掘。我为此激动不已:虽然我在英国有过不少发掘经验,但这一次是全新的体验。我驾驶着老旧的路虎从伯明翰一路开到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在那里转乘一辆更加老旧的公交车前往阿西罗斯(Assiros),我们的工作地点就在那个农庄。在那里,项目进入正轨。我们整天对史前陶器进行计数、称量和归类,等到夕阳西下,就在发掘现场尘土飞扬的前院里喝上一两杯茴香酒,养养精神。
某个傍晚,一个老人侧身骑着驴,用手杖轻敲坐骑,从发掘现场边上的土路经过。他旁边有个徒步行走的老妇,鼓鼓囊囊的麻袋压弯了她的背。他俩经过时,我的一个同学用蹩脚的希腊语问候他们。
老人停了下来,满脸笑容。他跟我们的代言人翻译聊了几句,然后两位老人继续向前跋涉。
“那是乔治先生。”我们的翻译说。
“你跟他聊什么了?”有人问道。
“就是问候了一句。还问他为什么不让太太骑驴。”
停了一会儿,有人问:“然后呢?”
“他说他们只有一头驴。”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古典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冲击。在伯明翰,男人骑着驴,却让太太费力扛着大麻袋,会被看作自私(甚至更糟)。然而在阿西罗斯,这么做却顺理成章,其理由也不言自明,以至于乔治先生显然觉得我们的问题很蠢。
三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我撰写本书,就是试图解释我在阿西罗斯的所见所闻。本书的内容基于2012年10月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的有关人类价值观的两次坦纳讲座。受邀主讲坦纳讲座是学术生涯的至高荣誉之一,但老实说,我这样的人本来不太可能受邀,所以这更令我备感荣幸。在遇到乔治先生之后的30年里,我从未写过有关道德哲学的只言片语。当然,那件事的细节让我犹豫不决,但仔细考虑之后,我确信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观研究中心实际上是我评论阿西罗斯事件的最佳场所,因为准确地解释乔治先生的话和我自己当时的反应,差不多就相当于一部近两万年来人类价值观文化演变的通论了。我认为,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历史和考古学,而非道德哲学的专业知识背景,我自忖,这样一部人类价值观文化演变通论,道德哲学家或许也会感兴趣。
至于我的观点正确与否,在看过专家点评之后,留与诸位评说。我在前五章陈述理论,第六章到第九章是4位应答者对原讲座的回应——他们分别是古典学者理查德•西福德、汉学家史景迁、哲学家克里斯蒂娜•M•科尔斯戈德,以及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但我将在第十章做总结陈词,对他们的回应作答。
过去这四五十年,针对我见到乔治先生、他的驴和他太太时所遭遇的那种文化冲突(以及比这更古怪的),学术界撰写的书籍和论文早已堆积成山。然而,我即将在本书中探讨的问题与大多数此类研究全然不同。在我看来,放眼整个地球过去两万年的历史,我们会看到人类的价值观经历了三个大致交替出现的体系。与每一种价值观相关联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而每一种组织形式又是由人类从周遭世界获取能量的特定方式决定的。归根结底,能量的获取方式不仅能够解释乔治先生说的话,也能够解释他的话为何令我大吃一惊。
不过我得抓紧时机补充一句:因为价值观体系——抑或文化,或者随你怎么称呼——是无形的存在,如果想用100多页的篇幅来论证这个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关注较为笼统的价值观体系中具体的子集。因此,我在本书中相对仅限于(包括政治、经济和性别的)平等与等级制度的观念,以及人们对待暴力的态度。之所以选择这些主题,部分原因是我对它们感兴趣,此外它们似乎也比较重要。不过我也怀疑价值观的大多数子集都会揭示同样的模式;如若不然,对价值观的不同子集进行比较就会成为一个明显的逻辑漏洞,批评家们就会借此曲解我的观点。
第二章到第四章,我将用三章的篇幅展示这三种大致先后交替出现的人类价值观体系的现实。第一种体系,我称之为“觅食价值观”,因为与它相关的社会主要通过采集野生植物和狩猎野生动物来维生。觅食者倾向于看重平等而非大多数类型的等级制度,也比较能够容忍暴力。第二种体系,我称之为“农业价值观”,因为与它相关的社会主要靠驯化的动植物来维持生计。农耕者倾向于更看重等级制度而非平等,比较不能容忍暴力。第三种体系,我称之为“化石燃料价值观”,它所关联的社会主要以已经转变为煤、天然气和石油的化石的能量来增加现存动植物的能量。化石燃料使用者倾向于看重大多数类型的平等而非等级制度,且非常不能容忍暴力。
这一框架不仅解释了1982年乔治先生的话为何让我觉得如此奇怪(他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农耕阶段,而我已经进入化石燃料阶段了),似乎也对我们研究人类的价值观产生了两个更为广泛的意义。如果我的能量获取方式决定价值观的观点是正确的,它或许能引出两个结论:(1)道德哲学家们力图找到一个整齐划一的、完美的人类价值观体系的努力是徒劳的,以及(2)我们(不管“我们”是谁)如今视若珍宝的价值观,实际上很可能——在并不十分久远的将来的某个时间点——变得全然无用。在那个时间点(前提还是如果我是对的),我们会抛弃这些价值观而进入第四个阶段,也就是“后化石燃料”阶段。在本书第五章,我提出了一些设想,探讨了那种价值观可能的形态。
我关于文化冲突的研究与大多数近期研究的不同,就在于我试图诠释这一经验而不仅仅是理解它。关于此二者的区别,往往要追溯到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社会学之父马克斯•韦伯。然而,韦伯并非第一个将理解与诠释 作为两种思考社会行为的方式对立起来的学者。这一荣耀似乎要归于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 ,他在19世纪50年代指出,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从事的活动从根本上完全不同。德罗伊森说,历史学家试图理解(这里是指抓住过去的行为者的主观意义)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家试图诠释(这里是指找到原因)研究对象。
韦伯不但极为详细地阐明了德罗伊森最初的表述,而且提出社会学有第三个目标,既不同于历史也不同于科学:将诠释与理解合而为一。他指出:“当公开的行为及其动机都已被正确理解,且与此同时其关联的意义已经完全能够被理解时,我们就能对某一具体行为过程的因果关系加以正确诠释……如果在意义方面还缺乏足够的依据,”他补充道,“那么不管二者之间存在多高的一致性,也不管其概率能够多么精准地计算出来,它仍然是一个不可完全理解的统计概率,不管我们讨论的是客观进程还是主观过程。”
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使得韦伯的思想在美国社会学界有了广泛的受众,而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他最初是帕森斯的学生)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它贴上了一个崭新的标签。“与马克斯•韦伯一样,我认为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格尔茨写道,“我觉得文化就是那意义之网,因此文化分析并非探索规律的实验性科学,而是寻求意义的诠释性科学。”在如此诠释韦伯的基础上,格尔茨认为,要想理解社会行为,就必须进行“长期的、主要是(但并非完全)量化的、高度参与乃至近乎着魔的搜索式田野调查”,从而产生了他所定义的著名标签——“深描”。
按照格尔茨的说法,深描通常应该采用“论文的形式,30页还是300页倒无所谓,这是提出文化诠释乃至该诠释之理论基础的天然体裁”。因此,“一部人种志能否得到关注……不在于它的作者能否在某个偏远的深山老林里获得原始资料,而在于他能够在何种程度上阐释在那些地方发生了什么,把关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的谜题简化为‘在未知背景下,会自然产生哪些我们不熟悉的行为’”。
1982年的那一天,我脑中确实闪过一个念头:乔治先生可能在跟我们开玩笑,讥讽我们这些第一世界的来客对其乡村生活方式的倨傲态度。然而事实确是乔治先生骑在驴背上,而他的妻子却背着个大麻袋徒步前行。我丝毫不怀疑,如果把乔治先生的话放在阿斯洛特(Assirote) 乡村生活的深描语境下,能够揭示一个陌生而奇妙的世界观。然而这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我的目标并非理解乔治先生和太太的行为,而是希望能够诠释它。
You may also be interested in the following product(s)
-

她们 The Group
£15.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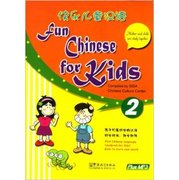


 Facebook
Facebook Twitter
Twitter Pinterest
Pinterest Google +
Goo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