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tails
基本信息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16年1月1日)
外文书名: Kafamda Bir Tuhaflik
作者:奥尔罕·帕慕克 Orhan Pamuk (作者), 陈竹冰 (译者)
平装: 556页
语种: 简体中文
开本: 16
ISBN: 9787208135505, 7208135509
条形码: 9787208135505
商品尺寸: 24 x 17 x 3 cm
商品重量: 739 g
品牌: 世纪文景
编辑推荐
如果将人界定为时代的产物,我们往往带着一种外部审视的态度去关注时代的英雄,或者记录时代的边缘者。但人的复杂与奇妙却在于他的内心对世界的映照,那些他脑袋里存在的“怪东西“,正是这个世界美妙的存在方式。《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正是这样一个独特的故事,它讲述了钵扎小贩夫鲁特的人生与幻想,洞察了一幅1969年至2012年间伊斯坦布尔生活的画卷。在这个变动的时代里,夫鲁特并没有成为主角。他走街串巷,经历不同的人和冒险,看到世事的变迁;商业、宗教、私奔和婚姻,一切的经历都如同一块块五光十色的琉璃,映照在他的心中,诞生出奇妙的景象。这本书是一部诚挚的作品,主人公心中孩子般的天真、好奇和对爱的笃定,让人为之动容。在他所构建的奇妙世界,伊斯坦布尔就是他的领地,他如同一个自由的精灵在飞舞,任凭时代在他俯身之下流淌。
——亚马逊编辑MI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的名字叫红》《伊斯坦布尔》作者奥尔罕·帕慕克 蛰伏六年动情写就 全球60个语种正在流行
斩获诺奖之后还能写出自己的作品,帕慕克就是这样的大师。——《独立报》
让一千万人聚集在伊斯坦布尔的东西是生计、利益和账单,但只有一样东西支撑着这茫茫人海中的人们,那就是爱
嘈杂腐败而又日新月异的城市史诗,天真、正派又卑微的街边小贩的人生传奇
媒体推荐
在奥尔罕·帕慕克的疯狂里有卓而不群的才华。
——翁贝托·埃科
帕慕克是健在的最伟大的作家。
——《观点杂志》
伟大、真挚,又令人动容的一部关于伊斯坦布尔的编年史,不同章节中细节的丰富程度可以媲美市面上任何单行本小说。帕慕克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社会政治激荡这一大背景下小人物们的日常。麦夫鲁特这个角色以及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都令人难以忘怀。
——《华尔街日报》
作者将一系列独到的视角、丰富的地理人文与激荡的社会变革等元素围绕在书中这位忧郁的主人公周围。因讲述街边故事而寻到其最真挚声音的叙述方式也让人感受到了作者大师般的笔法、学识上的丰腴、情感上的敏锐以及行文的自由。第 一人称的叙述也足够讨巧,也让这部关于麦夫鲁特的故事有了多彩而各异的声音。
——《纽约时报书评》
可以说是帕慕克作品里最令人愉悦的一本小说,也是新读者渴望深入了解这位文学大师很好的入口。帕慕克之于伊斯坦布尔就好似詹姆斯·乔伊斯之于都柏林。他不仅仅描绘到了城市的情感与风貌,还精准地捕捉到了这座城的文化、信仰、传统、价值观等最核心的部分。一部献给现代土耳其的情书。
——《华盛顿邮报》
帕慕克最真挚的同情,这次将视角聚焦到了一个人世浮沉的街边小贩身上,而这个跃然纸上的人物形象,在帕慕克的笔下变得和苏丹们一样崇高而富有意义。而帕慕克写作中让读者于渺小处见崇高的笔法也是我们阅读帕慕克的理由之一。《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仍然让人感受到一位好似年轻作者才有的生猛与野心。
——《旧金山纪事报》
一个有着独特韵味又令人回味无穷的叙述方式,小说中最令人的动容的章节是关于那些每日周旋于丈夫、岳父威权下女人们。
——《经济学人》
小说中丰富的细节创造了一个身临其境的世界,极大地刺激了读者们的感官、嗅觉乃至味蕾。而帕慕克的写作技巧也让那些看似艰深平淡的主题读起来超凡脱俗。
——《芝加哥论坛报》
在激荡变革的伊斯坦布尔,在东西交汇节点的伊斯坦布尔,帕慕克描绘了一个和家族与友人有关的人物群像,讲述的故事也和宗教国家经历现代化变革以及其中出现的不和音等主题息息相关。
——《波士顿环球》
帕慕克就是我们时代最优秀的小说家,《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的出版也意味着伊斯坦布尔跻身全球最伟大的文学都市之一。阅读帕慕克的过程,就好像一边细品红酒一边阅读狄更斯晚年的作品。
—— Counterpunch
优美的写作,字里行间里有着无尽的忧愁。这是一本复杂的长篇小说,作者绵密地展示他作为小说家的十八般武艺:无处不在的暗线、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繁复的引文。然而它也是一本回顾历史细节的小说,伊斯坦布尔四十年来的政治变革与人口流动与城中人物角色的日常交织在一起。这是一部关于都市现代化主题的小说,同时又有着对老城巨变前的哀叹。
——《金融时报》(UK)
帕慕克的这部作品触及了婚姻、父母养育以及略显嘈杂的大家族等主题。他也成为为数不多在斩获诺奖之后还能写出自己理想作品的大师级作家。
——《独立报》
这个寓言式小说的主角是一个老是沉浸在自我世界中进行思考回想的小贩麦夫鲁特。他的家族成员间的爱恨情仇极其吸引人,但是小说中最出彩的部分要算帕慕克笔下伊斯坦布尔的模样:嘈杂、腐败但又日新月异地经历变革。而读者在阅读中也好像随着他的笔触游历了这座帕慕克的故乡,这座极具文化魅力、政治情绪不稳定同时阶层分化、性别分化严重的城市。
——《出版商周刊》
帕慕克在作品里探讨了这座城市别具魅力的传统文化,并为传统文化被全盘抛弃写下挽歌,而在那些优美并极富感染力的文字里,作者游走于多种文体之中,有用记叙性的文字探讨伊市地产商人的阴谋、电力公司私有化进程的章节,同时也有着对人类外在与内心世界巨大鸿沟类似沉思录式的考量,让人想起了维多利亚时代伟大小说家们的写作。
——《科克斯书评》
作者简介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 1952—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生于伊斯坦布尔,自幼学画,大学主修建筑,后从文。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为60多种语言出版。
目录
第一章(1982 年6 月17 日,星期四)
麦夫鲁特和拉伊哈
私奔不易
第二章(1994 年3 月30 日,星期三)
二十五年里麦夫鲁特在每个冬天的夜晚
放开卖钵扎的人
第三章(1968 年9 月—1982 年6 月)
1.麦夫鲁特在村里时
这个世界要是说话,会说些什么?
2.家
城市尽头的山头
3.在一块空地上盖房子的有魄力的人
啊呀,我的孩子,你被伊斯坦布尔吓着了
4.麦夫鲁特开始小贩生涯
你没资格摆架子
5.阿塔图尔克男子高中
良好的教育可以消除贫富差距
6.初中和政治
明天不上学
7.埃雅扎尔电影院
生死攸关的一件事
8.杜特泰佩清真寺的高度
难道那里有人生活吗?
9.奈丽曼.
让城市成为城市的东西
10.在清真寺墙上张贴共产党海报的后果
保佑突厥人
11.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之间的战争
我们是中立的
12.从村里娶姑娘
我的女儿不出售
13.麦夫鲁特的小胡子
契地皮的主人
14.麦夫鲁特坠入爱河
这样的不期而遇只会是天意
15.麦夫鲁特离家出走
要是明天在街上看见,你能认出她来吗?
16.如何写情书
从你眼睛里射出的魔力之箭
17.麦夫鲁特服兵役的日子
这里是你的家吗?
18.军事政变
工业园区墓地
19.麦夫鲁特和拉伊哈
私奔殊非易事
第四章(1982 年6 月—1994 年3 月)
1.麦夫鲁特和拉伊哈结婚
有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
2.麦夫鲁特的冰激凌生意
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3.麦夫鲁特和拉伊哈的婚礼
卖酸奶人当中的可怜人是卖钵扎的
4.鹰嘴豆饭
不干不净的食物更好吃
5.麦夫鲁特当爸爸了
千万别下车
6.萨米哈的私奔
人为什么活在世上
7.第二个女儿
他的人生仿佛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一件事情
8.资本主义与传统
麦夫鲁特的安乐窝
9.加齐街区
我们将躲藏在这里
10.擦去城市的灰尘
我的真主,哪来的这么些脏东西啊?
11.不见媒婆的女孩们
我们顺道拜访一下
12.在塔尔拉巴什
世上最幸福的男人
13.苏莱曼挑起事端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14.麦夫鲁特在另外一个角落
明天一早我就去把它要回来
15.先生阁下
我遭遇了不公
16.宾博快餐店
千万别让人亏待你
17.员工们的阴谋
你什么也别管
18.在宾博的最后日子里
两万只羊
第五章(1994 年3 月—2002 年9 月)
1.连襟钵扎店
一件光荣的爱国之举
2.和两个女人待在一家小店里
别的电表别的人家
3.费尔哈特的电力爱情
咱们离开这里吧
4.孩子是一样神圣的东西
让我去死,你和萨米哈结婚
5.麦夫鲁特当停车场管理员
又愧疚又困惑
6.拉伊哈之后
如果你哭,谁也不能跟你生气
7.用电消费的记忆
苏莱曼遇到麻烦事
8.麦夫鲁特在最远的街区
狗只对异己号叫
9.整垮夜总会
难道对吗?
10.麦夫鲁特在警察局
我的一生都是在这些街道上度过的
11.内心的意愿和口头的意愿
法特玛还在上学
12.菲夫齐耶私奔
让他俩都来亲吻我的手
13.麦夫鲁特孑然一身
两人彼此这么合适
14.新街区,旧相识
这是一样的东西吗?
15.麦夫鲁特和萨米哈
那些信是写给你的
16.家
我们谨言慎行
第六章 (2009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三)
十二层的公寓楼
城市的外快是你应得的
第七章 (2012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四)
一座城市的外形和面貌
只有行走时,我才能思考
人物索引
大事记
文摘
麦夫鲁特和拉伊哈
私奔不易
这个故事讲述麦夫鲁特·卡拉塔什的人生和梦想。故事的主人公麦夫鲁特,一个叫卖酸奶和钵扎的街头小贩,1957年出生于亚洲最西端的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那里可以远望迷雾湖畔,却一贫如洗。十二岁那年,他来到世界之都伊斯坦布尔,便一直生活在这里。二十五岁那年,他从邻村抢了一个女孩,虽然其中发生了一些怪异的事情,但此举决定了他后来的一生。回到伊斯坦布尔,他结婚并有了两个女儿。他不停地劳作,做过各种营生,类似叫卖酸奶、冰激凌、米饭的小贩,餐馆服务员,但夜晚从未放弃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叫卖钵扎,也从未放弃构筑他怪异的梦想。
我们的主人公麦夫鲁特,高高的个子、健壮、谦和、英俊。他有一张激唤女人怜爱的孩子气脸庞,一头棕色的头发和专注、聪慧的眼神。不仅在年轻时,甚至在四十岁之后,他的脸上依然保留着稚气,依然是女人们心目中的俊男。记住麦夫鲁特的这两个基本特点,有助于对故事的理解,所以我会不时地提醒我的读者。至于麦夫鲁特的乐观和善良—某些人认为是单纯—就无需我提醒了,你们自会发现。如果我的读者也能像我这样结识麦夫鲁特,那么他们也会对那些认为他英俊和孩子气的女人表示赞同,相信我没有因为想给故事添彩而夸大其词。因此,我要说的是,在这本完全依据真实事件写就的书里,我不会采用任何夸张的叙述手法,对于那些怪异的事件,我仅以有助于更好地跟随和理解故事的形式,将它们一一呈现给读者。
为了更好地讲述主人公的人生和梦想,叙述将从故事的中间开始。首先说的是,1982年6月他和邻村一个女孩私奔的故事。邻村的名字叫居米什代莱,隶属于科尼亚市的贝伊谢希尔县。麦夫鲁特第一次见到那个自愿和他私奔的女孩,是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婚礼上,也就是他伯父的大儿子考尔库特于1978年在梅吉迪耶柯伊举行的婚礼。麦夫鲁特根本无法相信,他在伊斯坦布尔婚礼上见到的女孩也会喜欢自己,她很漂亮,还是个孩子(十三岁)。女孩是堂兄考尔库特的妻妹,因为姐姐的婚礼,她人生第一次来到伊斯坦布尔。麦夫鲁特给她写了三年情书,尽管他从未收到过女孩的回信,可是为他送信的考尔库特的弟弟苏莱曼,一直在给他希望,并让他继续写信。
即便在此刻抢亲时,苏莱曼依然在帮助叔叔的儿子麦夫鲁特。苏莱曼开着自己的福特小卡车,和麦夫鲁特从伊斯坦布尔回到了他们度过童年的村庄。两个朋友背着所有人,制订了抢亲计划。按照计划,苏莱曼将在离居米什代莱村一小时路程的地方,等待麦夫鲁特和他抢来的姑娘,当所有人认为两个恋人去了贝伊谢希尔方向时,他将载着他们朝北行驶,穿过群山,送他们去阿克谢希尔火车站。
麦夫鲁特仔细地把计划琢磨了四五次,冷洌的水池、涓细的小溪、丛林密布的山头、女孩家的后花园,诸如这些重要的地方,他都已偷偷地去察看了两回。半小时前,他从苏莱曼开的小卡车上下来,走进路边的村庄墓地,看着墓碑祈祷,祈求真主保佑他一切顺利。他不信任苏莱曼,这点他对自己都不敢承认。他想,如果苏莱曼没开车去水池边,那个他们约好的地方,怎么办?因为会搞乱脑子,他禁止自己去想这个可怕的问题。
麦夫鲁特身穿一件蓝色衬衫和一条新的布裤子,那还是早在他和父亲一起卖酸奶的中学年代留下的,是在贝伊奥卢的一家商店里买的,脚上的鞋还是当兵前从苏美尔银行开的商店里买来的。
天黑后不久,麦夫鲁特摸近了残缺的院墙。姑娘们的父亲是歪脖子·阿卜杜拉赫曼,他们住的白房子的后窗一片漆黑。来早了十分钟,他无法控制自己,不断朝那扇漆黑的窗户张望,他想起了过去抢亲时陷入血仇陷阱而被打死的人、黑夜奔跑时迷路而被抓的人、因为女孩最后一刻放弃私奔而尽失颜面的人。他迫不及待地站起来,告诉自己真主会保佑他的。
狗叫了,窗户亮了一下又黑了。麦夫鲁特的心狂跳起来。他走向房子,在树间听到了一声响动,女孩悄声喊着他的名字:
“麦夫—鲁特!”
这是一种充满爱怜的声音,来自一个读了他当兵时写的情书、信任他的人。他想起了那上百封蘸满爱情和渴望的情书,为了说服美丽的姑娘而愿意付出一切的承诺和美好的梦想,最终他成功地感动了姑娘。他什么也看不见,在这神秘的黑夜,他梦游般径直朝发出喊声的地方走去。
在黑暗中他们找到了彼此,自然地牵起手奔跑起来。但刚跑了十几步,狗就狂吠起来,麦夫鲁特慌乱中迷失了方向。凭着本能,他努力向前跑,但脑子一片混乱。夜色中树木忽隐忽现,犹如一堵堵水泥墙擦身而过,仿佛就在梦里。
就像计划中的那样,跑完羊肠小道,一段陡坡出现在麦夫鲁特的面前。岩石间蜿蜒而上的窄道越发陡峭,仿佛直指乌云密布的漆黑夜空。攀爬了近半小时后,他们继续在坡顶手牵手不停地奔走。在这里,可以看见居米什代莱的灯光,还有后面的杰奈特普纳尔,他出生长大的村庄。如果有人追来,为了不被抓回村子,甚至为了应对苏莱曼的另外一个秘密计划,麦夫鲁特凭着本能朝相反方向走去。
狗还在狂吠。麦夫鲁特明白,对于村庄,他已是一个陌生人,没有一只狗认识他。没过多久,从居米什代莱村方向传来了一声枪响。他们努力保持镇静,没有改变奔走的速度。当狗消停一阵后重新咆哮起来时,他们就从坡上往下奔跑。树叶和树枝划过他们的脸颊,荆棘刺透了他们的裤管。黑暗中,麦夫鲁特什么也看不见,只感觉他们随时会被石头绊倒,但这并没有发生。他惧怕那些狗,但他知道真主在保佑自己和拉伊哈,他们会在伊斯坦布尔过上幸福生活。
当他们气喘吁吁地跑到通往阿克谢希尔的路上时,麦夫鲁特确信他们没有迟到。如果苏莱曼也开着小卡车来了,那就谁也不能从他手上把拉伊哈抢走了。麦夫鲁特每次开始写信时,都会想一想女孩美丽的脸庞和那双无法忘怀的眼睛,都会在信头上,激动、仔细地写下她美丽的名字,拉伊哈。想到这些,他兴奋地加快了脚步。
现在,尽管在黑暗中他无法看清自己抢来的女孩,但他很想抚摸她、亲吻她,但拉伊哈用随身携带的包袱轻轻地推开了他。麦夫鲁特喜欢这样。他决定,结婚前不去碰这个将和他共度一生的人。
他们手牵手跨过萨尔普小溪上的小桥。拉伊哈的手就像小鸟那样轻巧纤细。从潺潺流淌的小溪,一阵浸润了百里香和月桂花香的凉爽拂面而来。
夜空闪过一束紫色的电光,随后传来了雷声。麦夫鲁特害怕在漫长的火车旅行前被雨淋湿,但他并没加快脚步。
十分钟后,他们远远看见了苏莱曼的车尾灯,卡车停在发出咳喘声的水池旁。麦夫鲁特幸福得快要窒息了。他为怀疑苏莱曼感到内疚。开始下雨了,他们开心地跑起来,但两人都累了,福特小卡车的尾灯比他们以为的还要远。跑到车旁时,他们已经被阵雨淋湿了。
拉伊哈拿着包袱,钻进了昏暗的小卡车后面。这是麦夫鲁特和苏莱曼之前计划好的:一来如果拉伊哈私奔的事被知道了,可能会遇到宪兵在路上搜车;二来拉伊哈不会看见和认出苏莱曼。
坐上前座,麦夫鲁特说:“苏莱曼,你的兄弟情谊,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情不自禁地用力拥抱了堂兄弟。
苏莱曼却没能表现出同样的兴奋,麦夫鲁特认为是自己的质疑伤了他的心。
苏莱曼说:“你发誓,不告诉任何人我帮了你。”
麦夫鲁特发了誓。
“女孩没把后门关上。”苏莱曼说。麦夫鲁特下车,在黑暗中朝小卡车的后面走去。当他面对着年轻女孩关下后门时,一道闪电划过,整个天空、山峦、岩石、树木,所有的东西瞬间如同遥远的记忆被照亮。麦夫鲁特第一次近距离看清了这个将成为他的妻子,并要和他共度一生的姑娘的面容。
他将在一生中,时常想起这一瞬间,这种怪异的感觉。
车开动后,苏莱曼从手套厢里取出一块抹布递给麦夫鲁特说:“拿这个擦擦。”麦夫鲁特闻了闻,确信不脏后,从卡车门框的小洞里把抹布递给了后面的女孩。
过了很久,苏莱曼说:“你还湿着,也没别的抹布了。”
雨点打在车顶发出噼啪的声响,雨刷则发出一种怪异的呻吟声,但麦夫鲁特知道,他们正在一种深邃的静默中前行。昏暗的橘黄色车灯前,树林黝黑阴森。麦夫鲁特听说过很多关于狼、豺、熊和地下幽灵半夜聚会的故事,也在夜晚的伊斯坦布尔街道上,遇见过很多传说中的怪物和魔鬼的影子。这种黑暗,如同尖尾魔鬼、大脚巨人、犄角独眼兽,抓住迷路的笨蛋和绝望的罪人后,将其投入的地下世界。
“怎么变哑巴了。”苏莱曼调侃道。
麦夫鲁特明白,他沉浸其中的奇怪静默将持续很多很多年。
他试图搞清楚,自己是如何误入人生设下的这个陷阱的,“因为狗叫了,我迷了路,所以就这样了。”他为自己寻找类似的理由,尽管他非常清楚这些理由是错误的,但因为可以从中得到安慰,他也就不情愿地相信了。
“有啥问题吗?”苏莱曼问道。
“没有。”
卡车在泥泞、狭窄的弯道处放慢了速度,车灯下,岩石、树木的幽灵、模糊的影子和神秘的物体一一跃入眼帘,麦夫鲁特全神贯注地盯着所有这些奇观,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切他将终生难忘。他们和狭窄的小路一起,一会儿蜿蜒向上,一会儿又盘旋而下,像小偷那样,悄悄地穿越一个消失在泥土里的黑暗村庄。村里的狗叫了起来,随后依然是深邃的静默,麦夫鲁特搞不清楚,这种怪异的感觉存在于他的脑海里,还是世界里。黑暗中,他看见了传说中的鸟影,看见了由奇怪的线条组成的字母,看见了几百年前经过这穷乡僻壤的魔鬼军队的遗迹,也看见了因为作孽而被石化的人影。
“千万别后悔。”苏莱曼说,“没什么可怕的。也没人追咱们。除了歪脖子爸爸,很有可能他们本来就知道女孩打算私奔。千万别跟任何人说起我,那时说服歪脖子·阿卜杜拉赫曼就容易了。过不了一两个月,他就会原谅你们俩。夏天结束之前,你和嫂子一起回去亲他的手,事情就过去了。”
在一个陡峭的坡上急转弯时,卡车的后轮开始在泥里打滑。那一刻,麦夫鲁特幻想到,一切都结束了,拉伊哈平淡无奇地回到了她的村庄,自己也平淡无奇地回到了伊斯坦布尔的家里。
然而,卡车继续前进了。
一小时后,车灯照亮了一两处农家,阿克谢希尔镇上的小街道。火车站在镇的另一头,在镇外。
“你们俩千万别走散。”苏莱曼把他们送到阿克谢希尔火车站时说。黑暗中,他朝拿着包袱等在那里的女孩看了一眼。“别让她看见我,我就不下车了。这下我也和这事脱不了干系了。麦夫鲁特,你一定要让拉伊哈幸福,好吗?她是你的妻子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你们在伊斯坦布尔稍微躲一下。”
麦夫鲁特和拉伊哈目送着苏莱曼驾驶的卡车,直到红色的尾灯在黑暗中消失。他们走进阿克谢希尔火车站的旧楼里,没有手拉手。
荧光灯把里面照得通亮。麦夫鲁特第二次看他抢来的姑娘,这回他近距离、屏气凝神地看了一眼。他确信了关后车门时看到的、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的事情,他移开了视线。
这不是他在堂兄考尔库特婚礼上看到的姑娘,而是她身旁的姐姐。他们在婚礼上让他看见了美丽的姑娘,现在却送来了她的姐姐。麦夫鲁特明白自己被骗了,他感到羞辱,他无法再去看这个连名字是不是拉伊哈都无法确认的女孩的脸。
是谁,跟他玩了这个游戏?走向售票处时,他听到自己脚步声的回音仿佛是别人的,那么遥远。老旧的火车站,将会在他一生,唤起他对那几分钟的记忆。
他买了两张去伊斯坦布尔的火车票,犹如他在梦中看到的一个人买了票。
“火车马上就来。”工作人员说。但火车没来。小候车室里满是篮子、大包、行李箱和疲惫的人们,当他们在一张长椅边上坐下时,彼此都没有开口说一个字。
麦夫鲁特想起,拉伊哈有一个姐姐,抑或是被他称为“拉伊哈”的美丽姑娘。因为这个女孩的名字确实叫拉伊哈,刚才苏莱曼是这么说起她的。麦夫鲁特也叫她拉伊哈,给她写情书,但在他的脑海里是另外一个人,至少是另外一张脸。麦夫鲁特也想到,他并不知道脑海里那个美丽女孩的名字。他不太明白自己是怎么被骗的,甚至想不起来了。而这,又把他脑海里的怪异感觉,变成了他深陷其中的那个陷阱的一部分。
坐在长椅上,拉伊哈一直盯着自己的手看。刚才他满怀爱恋地牵过这只手,他也曾在情书里写过想要牵到这只手,这是一只漂亮、柔滑的手。现在这只手乖乖地待在拉伊哈的怀里,时而仔细地把包袱或者裙子边整理一下。
麦夫鲁特起身,走去车站广场的小卖部买了两个面包圈。回来时,他又远远地仔细看了一眼拉伊哈戴着头巾的头和她的脸。当年他不听已故父亲的话执意去了考尔库特的婚礼,而眼前却不是他在婚礼上看见的那张美丽脸庞。麦夫鲁特再次确信,他以前从未见过这个真的叫做拉伊哈的女孩。可是怎么会这样呢?拉伊哈知道麦夫鲁特是想着她的妹妹写下那些情书的吗?
“你要吃面包圈吗?”
拉伊哈伸手接过了面包圈。麦夫鲁特在姑娘脸上看见的是一种感激之情,而不是私奔恋人们该有的激动神情。
拉伊哈做坏事似的怯生生地开始吃面包圈,麦夫鲁特在她身旁坐下,用余光瞄着她的一举一动。因为不知道该做什么,麦夫鲁特只好吃了那个不很新鲜的面包圈,尽管他并不想吃。
他们就这么坐着一句话也不说。麦夫鲁特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就像一个等待放学的孩子那样。他的脑子不由自主地不断琢磨,到底自己犯了什么错才导致了现在的糟糕局面。
他总是想起让他看见那个美丽姑娘的婚礼。去世的父亲穆斯塔法完全不愿意他去参加那场婚礼,但麦夫鲁特还是偷偷跑去了伊斯坦布尔。难道这就是他犯错的结果吗?麦夫鲁特内敛的眼神,就像苏莱曼的车灯那样,在他二十五年人生的灰暗记忆和影子里,探寻一种可以诠释现在这种情况的答案。
火车还是没来。麦夫鲁特起身又去了一趟小卖部,可小卖部关门了。两辆载客进城的马车在路边等着,一个车夫在抽烟。广场上一片寂静。他看见紧挨着车站边有一棵巨大的枫树,他走了过去。
树下立着一块木牌,车站灰暗的灯光照在木牌上。
我们的共和国缔造者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1922年来阿克谢希尔时
曾在这棵百年枫树下喝咖啡
学校的历史书上出现过几次阿克谢希尔的名字,麦夫鲁特也清楚这座邻镇在土耳其历史上的重要性,但这些书本上的知识,现在他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他为自己的无能而愧疚。上学时,他也没能尽力成为一个老师希望的好学生。可能这就是他的缺憾。今年他才二十五岁,他乐观地认为自己能够弥补缺憾。
他走回去,重新坐到拉伊哈身旁时又看了她一眼。不,他不记得四年前在婚礼上看见过她,哪怕只是远远的一瞥。
火车误点四个小时。他们在锈迹斑斑、发出悲鸣笛声的火车上找到了一个空车厢。尽管车厢里没有别人,麦夫鲁特还是坐在了拉伊哈的身旁,而不是她的对面。开往伊斯坦布尔的火车,经过道岔和铁轨的磨损处时都会不停地摇晃,那时麦夫鲁特的胳膊和肩膀,会不时碰到拉伊哈的胳膊和肩膀。对此麦夫鲁特也觉得怪怪的。
麦夫鲁特走去车厢的厕所,就像儿时那样,听到从金属蹲便器排污口传来的嗒克嗒克声。他回去时,姑娘竟然睡着了。出逃的夜晚她怎么可以如此安心入睡?麦夫鲁特在她耳边叫道:“拉伊哈,拉伊哈。”姑娘被叫醒,用一种真的名叫拉伊哈的人才有的落落大方,甜美地笑了笑。麦夫鲁特默默地坐到她身旁。
他们就像一对结婚多年后无话可说的夫妻那样,一起向窗外张望。偶尔他们看见一个小镇的路灯、行驶在僻径上的车灯、红绿两色的铁路信号灯,但多数时候窗外是漆黑的,车窗的玻璃上也只有他俩的影子。
两小时后天亮了,麦夫鲁特看见拉伊哈在默默落泪。火车在悬崖间一片紫色背景里呼啸着向前奔跑,车厢里只有他俩。
“你想回家吗?”麦夫鲁特问,“你后悔了吗?”
拉伊哈哭得更凶了。麦夫鲁特笨拙地把手放到她的肩上,但觉得别扭,又缩了回来。拉伊哈伤心地哭了很久,麦夫鲁特感到自责和后悔。
过了很久,拉伊哈说:“你不爱我。”
“什么?”
“你的信里全是情话,你骗了我。那些信真的是你写的吗?”
拉伊哈说完又继续哭起来。
一小时后,火车到了阿菲永卡拉希萨尔,麦夫鲁特跑下车,在小卖部买了一个面包、两块三角包装的奶酪和一包饼干。火车沿着阿克苏河前行时,他们从一个提着托盘卖茶的孩子那里买了茶,两人喝着茶吃了早饭。他们看到窗外的城市、杨树、拖拉机、马车、踢球的孩子、铁桥下流淌的河水,麦夫鲁特满意地注视着拉伊哈看着它们的目光。整个世界,一切都那么有趣。
火车开到阿拉尤尔特和乌鲁柯伊之间时,拉伊哈睡着了,她的头靠在了麦夫鲁特的肩上。麦夫鲁特从中感到了责任也感到了幸福。两个宪兵和一个老人上车坐了下来。麦夫鲁特把电线杆、柏油路上的卡车和新建的水泥桥,看作是国家日益富裕和发展的象征,但他不喜欢写在工厂、贫穷街区墙壁上的政治口号。
麦夫鲁特也睡着了,尽管他对自己的睡意感到惊讶。
火车到达埃斯基谢希尔时,他俩都醒了,看见宪兵的刹那间惊慌了一下,反应过来后马上放松下来,相视一笑。
拉伊哈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微笑使人无法相信她隐藏或者偷偷地做了什么。她的脸庞端庄富有光彩。麦夫鲁特逻辑上认为她和那些欺骗自己的人是同谋,可是看着她的脸,他又不得不觉得她是无辜的。
火车快到伊斯坦布尔时,他们开始聊天,聊路边的一排排大工厂、从伊兹密特的炼油厂那高高的烟囱里喷吐出来的火焰、货轮到底有多大、它们将去往世界的哪个角落。拉伊哈与她的姐姐和妹妹一样读完了小学,所以她可以轻松地说出那些遥远的沿海国家的名字。麦夫鲁特为她感到骄傲。
尽管拉伊哈四年前因为姐姐的婚礼去过一次伊斯坦布尔,但她还是谦逊地问道:“这里是伊斯坦布尔吗?”
“这里是卡尔塔尔,算是伊斯坦布尔了,”麦夫鲁特自信地说,“但还差一点。”他指着对面的岛屿给拉伊哈看。他想,终有一天他们会去那些岛上游玩。
但在拉伊哈短暂的一生中,他们竟一次也没去过。
You may also be interested in the following product(s)
-

中国画线描:百蝶画谱
£8.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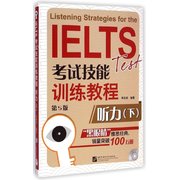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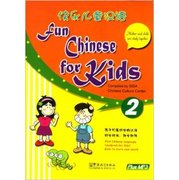

 Facebook
Facebook Twitter
Twitter Pinterest
Pinterest Google +
Goo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