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第1版 (2012年1月1日)
- 外文书名: The Painters Practice:How Artists Lived and Worked in Traditional China
- 丛书名: 高居翰作品系列
- 平装: 199页
- 语种: 简体中文
- 开本: 16
- ISBN: 9787108037541, 7108037548
- 条形码: 9787108037541
- 商品尺寸: 24.4 x 17 x 1.2 cm
- 商品重量: 381 g
- 品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Details
基本信息
编辑推荐
《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是高居翰作品系列之一。
媒体推荐
始终忠于自我,创作伟大作品,不必考虑日用所需及烦扰的文人画家神话在中国已经被珍视了上千年。在《画家生涯》中,高居翰富于想象地昭示出这一神话背后的现实。他让我们看到家庭作坊和被雇佣的代笔者,看到中间人、造伪者以及交易代理人,看到画家的画室以及技巧展示,看到顾主为得到画作而支付的形形色色的报酬:从糕点、药物、创作材料,一直到稀有的古董和迷人的侍妾。
——吏景迁(耶鲁大学教授)
高居翰是一位多产而受尊敬的中国绘画史学者,本书以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系列讲座为基础修订而成,讲述了历史上中国画家的创作情境,有趣可读。作者认为,中国文人画家的观点被中国和西方学者视为正确无误地加以接受,但根据信笺、笔记、题跋等历史记述,这一观点需要被重新检视。高居翰所讨论的事例包括文人画家如何卖画、画室的批量生产,以及由画家签名的代笔之作等。尽管这些议论是针对先前的学者而发,但读者只需对中国绘画略有了解便可明白其意。
——Library Journal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高居翰 (James Cahill) 译者:杨宗贤 马琳 邓伟权
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年出生于美国加州,是当今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权威之一。1950年,毕业于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之后,又分别于1952年和1 958年取得安娜堡密歇根大学艺术史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追随已故知名学者罗樾(Max Loehr),修习中国艺术史。
高居翰教授曾在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服务近十年,并担任该馆中国艺术部主任。他也曾任已故瑞典艺术史学者喜龙仁(Osvald sir6n)的助理,协助其完成七卷本《中国绘画》(Chinese Painting:Leading Master and Principles)的撰写计划。自1965年起,他开始任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的艺术史系,负责中国艺术史的课程迄今,为资深教授。1 997年获得学院颁发的终身杰出成就奖。
高居翰教授的著作多由在各大学授课时的讲稿修订或充分利用博物馆资源编纂而成,融会了广博的学识与细腻、敏感的阅画经验,皆是通过风格分析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典范。重要作品包括《中国绘画》(1960年)、《中国古画索引》(1980年)及诸多重要的展览图录。目前,他正致力于撰写一套五册的中国晚期绘画史,其中,第一册《隔江山色:元代绘画》、第二册《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第三册《山外山:明代晚期绘画》均已陆续出版。
1978至1979年,高居翰教授受哈佛大学极负盛名的诺顿(Charles Eliol Norton)讲座之邀,以明清之际的艺术史为题,发表研究心得,后整理成书:《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该书曾被全美艺术学院联会选为1982年年度最佳艺术史著作。1991年,高教授又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班普顿(Bampton)讲座之邀,发表研究成果,后整理成书:《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
目录
三联简体版新序
英文原版序
第一章 调整我们对中国画家的印象
关于郑呅的个案分析
绘画的业余化
后期鉴赏活动的影响
重新解读画作:应景之作
重新解读画作:山水画和手卷
第二章 画家的生计
图画的用途
获取一幅画作之一:委托和书信
获得一幅画作之二:中间人和代理人
获取一幅画作之三:市场和画室
买画付款的方式之一:现金支付与价格
买画付款的方式之二:礼物、服务和恩惠
买画付款的方式之三:盛情款待寓居画家
幕府、画院、女性画家
第三章 画家画室
顾主决定权的比重
情非所愿的画家
不满意的顾主:待审批的稿图
粉本和画稿
写生与临摹旧范本
画家画室
使用助手
第四章 画家之手
题材范围的缩小
不同类型的画家:地位和风格
笔法类型:风格与地位
文人画家及其受众
赝造画家之手
代笔者
董其昌及其代笔者
金农及其代笔者
注释
参考书目
图版目录
索引
序言
北京三联书店将在2009年陆续出版我的五本著作,为此我感到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因为它们终于有机会以精良的品相与大多数中国读者见面了。以前,虽然其中有两本出过简体中文版,但可惜那个版本忽视了图版的重要性,书中图片太小,质量也不够理想,无法充分传达文中所讨论的画作的视觉信息。事实上,如果缺少了这些图片,我的写作几乎是没有意义的。
近些年,为庆祝我自1 993年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退休十五载,并贺八十(二)寿辰,从前的学生和朋友们为我举办了各种集会活动,让我有充裕的时机来发挥余热。在“长师智慧”(Wisdom of Old Teacher)系列演讲中,我总结了自己一生研究中国绘画的基本原则。除了那些让我沉溺其中的随想与回忆,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一直在思索的:即中国绘画史研究必须以视觉方法为中心。这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要排除其他基于文本的研究方法,抑或是对考察艺术家生平、分析画家作品,将他们置身于特定的时代、政治、社会的历史处境,或其他任何新理论研究方法心存疑虑。这些方法都有其价值,对我们共同的研究课题都有独特的贡献。我自己也尽量尝试过所有这些研究方法,尽管并不充分。但是,正如以前我常对学生所说的,想成为一个诗歌研究专家,就必须阅读和分析大量的诗歌作品;想成为一个音乐学家,就必须聆听和分析大量的音乐作品。如果有人认为,不需全身心沉浸在大量中国绘画作品,并对其中一些作品投入特别的关注,就可以成为一名真正能对中国画研究有所贡献的学者,那么我以为,这实在是一种妄想。
然而,这种错误观念却广为传布。有些中国同事对我说,以他们对中国出版物的了解——远远超出了我有限的中文阅读水平——来看,国内学术界仍在很大程度上拘泥于文本研究,而忽视了视觉研究的方法,以为只有那样才是符合“中国传统”的,而所谓“风格史”研究则源于德国,从根本上说是西方的,不适用于中国。我最近在一些文章中(参见注)提到过这个问题。首先,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美国与欧洲兴起的中国绘画史研究之所以取得蓬勃发展,靠的并非一己之力,而是由于因缘际会,恰好融合了中国、日本、欧洲大陆、英国、美国等各地的学术传统。这其中当然也得益于向中国学者的学习:方闻、何惠鉴、曾幼荷、吴讷孙,以及收藏鉴赏家王季迁等人,他们无论在艺术史的文本研究还是视觉研究方面都是专家。第二,中国古代学者,如明清时期的思想家、绘画评论家董其昌等,也曾深入鉴赏活动当中,并从视觉角度对一些作品进行了分析,虽然我们今天只能看到他们留下的文字,但当初他们针对的可是亲眼所见的画迹。如果说他们的方式看起来与我们有所不同,那只是因为,当时除了木版印刷这种十分有限的媒体,他们缺乏其他更好的复制和传播图像的途径来传达其视觉感受。因此,他们在表达自己独特的体验与见解时,视觉因素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可以说,传统中国绘画史研究之所以特别重视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当时传播途径的限制。
今年三联书店将会出版我的四本书——《隔江山色》、《江岸送别》、《山外山》三本勾连成一部完整的元明绘画史,另外还有一本是《气势撼人》——它们在叙述与讨论时,都特别倚重对绘画作品的解读。读者很快就会发现,在前三本书中,讨论特定作品与风格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对元明绘画史其他方面的描述,而《气势撼人》每一章都以对某一幅画的细读或两幅画的比较为开篇,其后的论述均由此展开。事实上,这本书最初源于1979年我在哈佛大学的一系列演讲,它是我对如何通过细读画作和作品比较来阐明一个时期的文化史而作的一次尝试。在这本书的英文版序言中,我曾写道:“关于绘画,明清历史究竟能告诉我们些什么?这不是我关心的主题。相反,我所在意的是:明末清初绘画充满了变化、活力与复杂性,这些作品本身,向我们传达了怎样的时代信息,以及这样的时代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张力?”我的其他作品和文章,包括三联书店2011年出版的《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同样会进行大量的作品分析,但这样做只是为了说明情形和阐发论点。我不会一味地为视觉方法辩护,即使它确实存在局限也熟视无睹,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凡是有利于在讨论中有效阐明主旨的方法,我都会尽力采用。我也并非敝帚自珍,视自己的文章为视觉研究的最佳典范,这些文字还远未及这个水准。我所期望的是,这些尚存瑕疵的文字能够对解读和分析绘画作品有所启发,并引起广泛讨论。除了三联书店将会出版的这五本书,中文读者还能接触到我的另外两篇论文,它们同样可以用来说明我的治学方法。其中一篇研究了清初个性桀骜的艺术大师八大山人的作品如何体现了他的“癫症”(即他如何从自己过去的癫狂经验中获取灵感,使画作充满与众不同的气质);另一篇则试图梳理出一个中国明清绘画中可能存在的类别,其主要观众和顾客都是女性。
当然,相信大家也能举出和推荐很多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在讨论中国绘画问题时,会比我更好地运用视觉研究方法。由于我对中文著作掌握得非常不充分,因此无法将他们逐一列出,即使做了,那也将是一个糟糕的列表,很可能会漏掉一些优秀的作品而网罗进一些禁不起推敲的例证。不过,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以及所有研究中国绘画的外国学者,终其一生都在仰赖中国前辈和同行的著作,没有他们,我们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20世纪50年代,当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就很幸运地遇上了对我影响甚伟的导师之一,大鉴藏家王季迁。后来,我又在中国学术界结识了许多挚友。自从1973年作为考古代表团成员第一次去中国,1977年作为中国古代绘画代表团主席第二次去中国,直到此后多次非常有意义的访问与停留,我与无数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大学和艺术院校的教授、艺术家、学者等等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慷慨帮助让我接触到许多前所未闻的资料,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晚期写作。我对他们的感激难于言表。
倡导视觉研究方法并不困难,但这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如何能让那些希望运用这一方法的人看到高质量的绘画图像,获得研究所必需的视觉资料呢?我和很多外国学者接触图册、照片、幻灯片并不困难,不少人还能幸运地拥有自己的收藏。但这对大部分中国学者和学生来说,还存在相当困难。如今,解决这一问题有个可行的办法,那就是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图片数据库,这样使用者就可以在网络或者光碟上找到所需的资料了。当然,这项工程要靠年轻的数字图像技术专家们来完成,但如果需要图片资源或专家建议,我也一定会在有生之年尽己所能为此提供帮助,我确实打算这样做。
最后,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所有正在阅读它的中国读者,并祝愿中国绘画史研究拥有美好的未来,愿中外学者都能秉持互利协作的精神为之努力。
文摘
插图:

金农雇请的其他代笔画家中有一位叫朱筠谷的,据说他收过金农十多份委托作画的书函;另一位姓杨;以及金农的弟子罗聘,他后来也成为一位知名画家,并会“请师题跋”于他的仿作之上,“众竞相购之”。一幅金农题款的钟馗图【图4.25】极类罗聘的人物画,足以让人怀疑是罗聘为其代笔之作。甚至金农的好友郑燮也似乎涉足了金农书画的生产链,郑燮在一首诗中写道:“西园左笔寿门书(指高凤翰的左手画和金农的书法,人们均趋之若鹜),海内朋友索向余,(出自他们手笔的)短札长笺都去尽,老夫赝作也无余。”
金农到了1748年前后才转以绘画作为主要经济来源,当时他年约六十五六。此前,他曾经是个行商,以贩售古董为生,也出售砚台、纱灯之类物品。他的助手磨石成砚及制作纱灯;金农则于砚石上题写有待镌刻的砚铭、在纱灯上以他奇怪的书法和特异的绘画作装饰,通过这些添加将它们从手工艺制品提升至艺术品的层次,并且相应地增加了它们的市场价值。因此,他已习惯于将他的笔触与品味当作可供售卖的商品来考虑。他实际上已如斯维特拉纳·阿尔佩斯评论伦勃朗那样,成为“一名本我的企业家”。
阿尔佩斯所描述某些伦勃朗的所为与处境,与金农惊人地相似。(两位画家在其他绝大多数方面,如媒介和主题和风格,皆有天壤之别;我的用意只在说,类似的经济和社会艺术史状况,能激起画家做出相似的反应。)她写道,伦勃朗“让自己成为自由的个体,不必对赞助人担负义务,但却反而受制于市场”(第88页)17世纪的荷兰,如同18世纪的扬州,艺术生产顺应于商业文化,产生了数量较大、售价相对低廉的艺术品,主要卖给普通的中层民众,这些人在欧洲被称作中产阶级,他们从普遍的经济繁荣中足够受惠,开始有能力购入艺术作品(第94页)。这种情况的影响之一便是促使画家采用耗时较少的绘画方式,包括使用较松动不严谨的用笔。通过不再把润饰仔细、材料精美、费工费时以及如实描绘等这些标准作为衡量画作价值的基础,伦勃朗(以及金农和董其昌)从顾主手上夺走了决定所收到的作品能否被接受的特权(第98-99页);顾主得到的不是一件符合预先设想和既定标准的作品,而是一幅伦勃朗(或一幅金农、一幅董其昌)的作品,一幅超越常规批评之外的作品。阿尔佩斯写道,伦勃朗“制作了史无前例的艺术,然后将之商品化”(第98-99,110页)。
You may also be interested in the following product(s)
-

初学者之友:工笔禽鸟
£7.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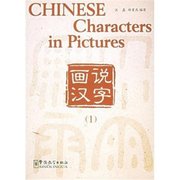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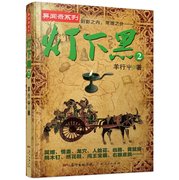



 Facebook
Facebook Twitter
Twitter Pinterest
Pinterest Google +
Goo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