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第1版 (2009年8月1日)
- 外文书名: Hills Beyond a River
- 丛书名: 高居翰作品系列
- 平装: 207页
- 高居翰(James Cahill) (作者)
- 语种: 简体中文
- 开本: 16
- ISBN: 9787108030108
- 条形码: 9787108030108
- 商品尺寸: 24.4 x 17 x 1.4 cm
- 商品重量: 440 g
- 品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Details
基本信息
编辑推荐
《隔江山色》是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
媒体推荐
《隔江山色:元代绘画》是中国晚期绘画系列著作五册的第一本(陆续有《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山外山:晚明绘画》及计划中的清代与近代绘画出版),学习中国画史的学生,也终于有一本讲究架构、尝试把艺术品和艺术家联系起来的教科书。
——何传馨(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副研究员)
高居翰教授……最可钦佩的特色,一是描述画史的变迁,能扣紧时代、社会、文化、思潮乃至文学的发展脉络来论述,极富深度与广度……另一个特色是对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绍不是一般概念化的陈述,而是极细腻的鉴赏与分析,不但深入浅出,引人人胜,而且以这种实证的方法,非常雄辩地印证了他的史观。至于时常以中西艺术史的轨迹来对比说明,对画史、画迹的资料巨细无遗的排比解析,充分显示作者知识博洽,见解独到,令人击节。
——何怀硕(台湾艺术学院教授)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高居翰(James Cahill)
高居翰(James Cahill),教授,1926年出生于美国加州,是当今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权威之一。1950年,毕业于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之后,又分别于1952年和1958年取得安娜堡密歇根大学艺术史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追随已故知名学者罗樾(Max Loehr),修习中国艺术史。 高居翰教授曾在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服务近十年,并担任该馆中国艺术部主任。他也曾任已故瑞典艺术史学者喜龙仁(Osvald Sir6n)的助理,协助其完成七卷本《中国绘画》(Chinese Paintin9:LeadingMasters and Principles)的撰写计划。 自1965年起,他开始任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的艺术史系,负责中国艺术史的课程迄今,为资深教授。1997年获得学院颁发的终生杰出成就奖。 高居翰教授的著作多由在各大学授课时的讲稿修订或充分利用博物馆资源编纂而成,融会了广博的学识与细腻、敏感的阅画经验,皆是通过风格分析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典范。重要作品包括《中国绘画》(1960年)、《中国古画索引》(1980年)及诸多重要的展览图录。目前,他正致力于撰写一套五册的中国晚期绘画史,其中,第一册《隔江山色:元代绘画》、第二册《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第三册《山外山:晚明绘画》均已陆续出版。第四、第五册仍在撰写中,付梓之日难料,但高居翰教授已慷慨地将部分内容及其他讲稿、论文刊布于网络,有兴趣的读者可登录www.jamescahill.info参阅。 1978至1979年,高居翰教授受哈佛大学极负盛名的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讲座之邀,以明清之际的艺术史为题,发表研究心得,后整理成书:《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该书曾被全美艺术学院联会选为1982年年度最佳艺术史著作。1991年,高教授又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班普顿(Bampton)讲座之邀,发表研究成果,后整理成书:《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
目录
三联简体版新序
致中文读者
英文原版序
地图
第一章 元代绘画的肇始
第一节 元代画坛的变革
第二节 业余文人画
第三节 元代的读书人
第四节 遗民
郑思肖
龚开
钱选
第五节 赵孟頫
第二章 山水画的保守潮流
第一节 赵孟頫的同辈与传人
高克恭
陈琳
盛懋
第二节 吴镇
第三节 马夏画派的传人
孙君泽
张远
第四节 李郭派的传人
唐棣
姚彦卿
朱德润
曹知白
第三章 元代末期山水画
第一节 元四大家其中三位
黄公望
倪瓒
王蒙
第二节 方从义
第三节 次要的苏州画家
马琬
赵原
陈汝言
徐贲
第四章 人物、花鸟、墨竹与墨梅
第一节 元代的人物画
颜辉与达摩图
因陀罗
刘贯道
张渥
陈汝言
任仁发
第二节 花鸟画
孟玉涧
陈琳
王渊
第三节 竹、兰、梅
李衍
吴太素
王冕
普明
赵孟頫
第四节 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
吴镇
倪瓒
注释
参考书目
序言
本书是所拟中国晚期绘画史一套五册中的第一册。其中有数册已经着手准备,希望在五年之内完成整套系列。其余四册将探讨明清两代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绘画。每册预计自成单元,分别包含晚期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如此一来将在范围上比拟——我原来也有此雄心——欧洲绘画中讨论文艺复兴(Renaissance)、巴洛克(Baroque)或其他时期绘画的著作。
一如每册自成单元,即使往后再有早期至宋代绘画的论著,这一套五册也可以独立。本册始于十三世纪末,那时中国绘画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这似乎是引领读者从中切入看中国画史。诚如后文各章显示,中国晚期绘画史始于元代,是个崭新的时期,而不只是旧世代的延续(虽然若干主题古已有之),是以非常值得纳入此一系列做个别介绍。
直到三十年前,远东以外的一些国家才开始严谨地研究中国晚期绘画,而且仍然有些争议。过去通常以为十三世纪末以降的绘画是鼎盛传统随宋代而亡,至少是明显式微之后每况愈下的产物。喜龙仁(Osvaldsiren)在《中国晚期绘画史》(HistoryofLaterChinesePainting)(1938年)之中,提纲挈领介绍了重要的画家、画派,刊出其代表作,但是他对十三世纪画风和美学背景与前代的差异这个基本问题着墨不多。其他的著者像司百色(WernerSpeiser,)和罗樾(MaxLoehr)(见参考书目1931与1939年的著作)则觉察到艺术价值上影响深远的转变藏在元代大师辉煌的成就之中。但是彰显那些艺术价值,从而熟悉这个广大而迷人的新领域,除了在中国与日本之外,往往碍于无法观览此一时期的真迹,仅有效果不彰的复制片,致使研究中断。直到1950年代情况才有改变,美国与欧洲两地的美术馆以及私人收藏家的典藏开始可以与远东国家并驾齐驱,而研究中国艺术的专家逐渐转移心力,从早期绘画移向晚期。
1950年代之后二十年间,中国绘画的研究进入百家争鸣的阶段。如今讨论宋代以后大师的文章多见于单篇论文、专书或博士论文,不是已经完成便是正在进行之中。画家传记资料渐趋完备,有助于澄清生平,许多中国画家与评论家的相关著作也有了翻译本。而最重要的是,风格的研究让画家与作品能在艺术史上定位明确,各个时期、画派与大师重大的贡献获得肯定,于是现在再写中国绘画史自然能从这些专门的研究中获益不少,我的收获可以从注解与参考书目中一目了然。
文摘
插图:


第一章 元代绘画的肇始
第一节 元代画坛的变革
十三世纪晚期,蒙古人推翻南宋政权,建立新王朝,是为元朝,中国绘画晚期的历史便在这改朝换代之际开展。宋朝由汉人皇帝世代相传,从公元960年到1279年,达三百余年之久;元朝自1279年起到1368年倾覆,大约只统治中国九十年,之后由另外一个国祚绵长的汉人政权明朝(1368-1644)所接替。对中国人而言,元代这段期间经济凋敝,生灵涂炭,精神抑郁苦闷。不过这个时代在文化上有好几个艺术领域却生气蓬勃,特别是戏曲、书法和绘画。其中尤以绘画为然,画史上正在酝酿一场空前的革命;元代以后的绘画除非刻意的模仿,面貌与1300年之前几乎完全不同。研究中国晚期绘画时,了解元代诸大家的成就非常重要,就如同研究欧洲绘画须先了解文艺复兴,道理是一样的。
艺术革命的原因可能比政治革命更难界定,但是若因此而说没有原因存在,也不尽然,变数总是来自艺术传统之内与艺术传统之外,两相激荡而共同决定新的方向。某些人有时候会指称,宋代的绘画气数已尽,多少注定要走下坡,即使宋朝国势仍然强盛,画风依旧有被取代的危险;这便是把艺术当作可以完全无视于历史影响,而独立发展。但事实上,元代画坛上的革命部分是由历史促成的。南宋(1127-1279)画坛上势力鼎盛的流派当属杭州画院,代表的大师是马远和夏珪【图1.1、图1.2]。院画在当时能独领风骚,不仅因为他们的作品有艺术上的实力和无与伦比的魅力,还由于与皇室的渊源而带来的权威。虽然他们在画坛上的势力稳若磐石,王朝一旦倾覆,一样无法幸免于难。宋朝的王室直到1276年才退出杭州,但是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1215-1294)所领导的蒙古政权,早在几十年前便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杭州的画院似乎也在十三世纪中期之后不久便停止了活动,也许是战乱所带来的压力所致。院画中那种典型的安逸气氛,无论如何大概是不适合这个时代了。
画院在杭州正当极盛之时,宋代早期遗留下来的旧派绘画,便由北方金朝的中国画家延续着。金朝,一称女真,这支异族,从十二世纪早期便统治北方地区,与南方的南宋属于同一个时期,1234年遭蒙古人驱逐。金朝治下的中国画家那种十分保守、甚至落伍的画风,并没有随着金朝的倾覆而消失,反而到了元朝还继续存在,后文将会讨论到。不过,元人入侵所带来的混乱与困顿,无可避免地会阻断各种严肃与大规模的绘画创作;在烽烟四起的乱世中,画家不太可能得到赞助,也不会有合适的工作环境。
除了历史因素之外,赞助也是一个重要的变数,因为所有宋代主要的绘画都是职业性的,画家们以卖画维生,或者在宫廷服务,或者有其他赞助。如今,在元代,这样子的传统隐而不彰了,幕前活跃的则是业余画家。早在十一世纪晚期,就有一群业余的文人画家崛起,开创了新的绘画流派,或者说是趋势,原称士大夫画,后来称为文人画。但是这股业余趋势,在宋代却未对职业画家造成威胁,到目前为止原因尚未充分探讨。十二世纪及十三世纪早期,有些文人画家在北方金朝从事创作,有一些则在南方地区。。禅寺中的僧人画家,就其风格与业余身份而言,与这些文人画家有些近似。十三世纪禅画兴盛,也见画院衰微,也许是反映了在外界动荡不安之际,禅寺提供了一个比较安稳的场所。
但是直到元初,业余画家还是停留在画坛的边缘。然后突然——一部分是因为职业画派的没落,一部分是因为业余画家令人振奋而且深具影响力的新发展——画家们发现自己(也开始以为自己)是居于画坛的核心。往后的中国绘画史中,除了明初有院画的短期复兴之外,业余画家便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于是,业余画家的崛起,伴随着绘画品味、创作风格和偏好主题的转移,构成了元代绘画变革的基础。画家来自与以前不同的社会阶级,他们各有不同的背景、理想与动机,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为不同的人作画,绘画不由自主地发生了根本而深远的改变。
第二节 业余文人画
中国宋代及宋以后,文化上的主要担负者是儒士,即士大夫。他们的文化活动包括编写史传,注释并传布经书,创作诗词及各类文学(包括现在认为最通俗的文学——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曲),作曲奏乐,尤其独占了书法艺术,除此之外,在宋代以后,大部分的绘画运动也是由他们推展。士大夫们彼此沟通讯息以及阐明思想的主要媒介自然是散文;但诗词、书法以及音乐,从很早以前便被视为较含蓄婉转的达意工具,是一种表现艺术,可借以将情意的微妙色彩、变动不居的心绪、个人心灵的特质加以具体化,而与其他的心灵交流。至于绘画,只要还在职业画家或“画匠”(文人口中的贬抑之词)的范围,便不可能被视同那些遣怀述志的表现艺术,而只是一种后天磨炼而来的技艺,只能创造供人玩赏的奇珍异宝。就是因为如此,文人不屑于从事绘画。不过,在宋代,由于画风与画论两方面有新的发展,绘画得以融合诗艺与书法,成为文人闲暇时的消遣。
事实上,文人适当的出路只有一种:即入朝为官。在宋代以前好几个世纪,便已经存在着士大夫阶级,他们与世袭的贵族之间有一种互为消长甚至是紧张的关系。中国早期历史中,官员一般出身世族;社会阶级之间的流动相当少。但是到了宋朝,虽然依旧可以透过皇亲贵族去谋得一官半职,但是大部分的官员皆是通过科举考试,凭着他们精通文理、博览经籍的真才实学而晋身仕途。入朝为官的人,不论天子脚下的朝中大臣,或地方上的小官吏,他们的教育、名望与权力都与社会上其他的族群有所区别。他们还有其余的特征:因为本身既有文学素养又有闲暇时间,所以文化水准颇高,对他们来说,这种文化水准或多或少变成是必须具备的;随着较高的文化水准便出现了崇古的心态,这种心态使得博古之风昌炽,也激发他们争相仿古,而在文学或艺术创作中,便也喜欢将古圣先贤的作品旁征博引一番。因为这些文人的教育是以先秦经籍与后世大量的注疏为基础,出现这种心态也是自然而然的。对传统的中国人而言,所谓的做学问,指的是钻研经典以及自出新注。知识性或社会性的议题,往往是借着对经典的注疏来加以陈述、讨论、甚至解决。
结果,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廷,但是科举却没有考察他们统理朝政的知识;也没有像性格测验一般检验他们是否能胜任行政工作。反而,考的是对经典是否熟悉,及有无能力提笔为文,讨论典籍中所见的原则如何落实于现实问题。以此观点类推,研究经典能让读书人行事有依据,心智有涵养,因此按理说来,他们可以根据有别于专家的考虑,因时因地做出正确的决策。日常的例行公事,便交给受过特别训练的僚属。于是士大夫的见解顺理成章偏向业余立场,与专业的立场形成对峙。当文人从事于绘画,而小心翼翼地避开与专业画家相关的风格特色,就显示了相同的偏见。如果一个人的画用了亮丽的色彩以及装饰性的图案来吸引观众的目光,可能这幅画就是出售用的。而绘画的正当动机,读书人认为,是要“寄兴”,这种活动本身的价值是在于修身养性;作品不可用来出售,只宜投赠知音。若在画中卖弄自己对于实物的描写如何几可乱真,便是屈从一般大众的写实口味了,而且也触犯了文人画的创作规范,这些我们往后会讨论到。强调技巧(我们先假定画家一定具备画技,但其实许多文人画家只具备某一方面,而且是相当有限的技巧)意味着只要磨炼技巧,即可以在绘画上登峰造极。而文人画家的想法正好相反——绘画的精神主要来自画家本身优异的禀赋,而绝少由后天技法造就,这种精神敏锐的鉴赏家看得出来,常人则容易失之交臂。此即所谓的“观画知人”。画家必备的修为并不是一般的“习画”训练,而是糅合了几项功夫:比如锻炼自己对风格的感受力;通过揣摩古画来熟习古代的风格;借书法提升笔墨功夫;而且无时不浸淫在大自然及文化的氛围中,使自己的感悟力和品味日益精进。
欧洲艺术史上也曾经发展出类似的文人业余画论,以为艺术家秉持自身的学养以及人格,应勘破利字这一关。这其实是陈义过高,易流于空言;而理想高于实际的状况,在西方可是更甚于中国,结果这种理论在西方绘画上的实质影响亦远低于中国。古希腊的艺术家早已考虑到一个问题:艺术到底应该被视作一项技艺,或是一门令人尊敬的行业。传说当时有画家拒绝接受酬劳,甚至将画作平白送人,以免沾染商业气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基本上还属于人文艺术,并且进而成为值得有学养的人投身的行业,他们以兼通文学与哲学来提升自己作品的水准;阿尔贝蒂(Alberti)1436年所写的《论画》(OnPainting)便是这种新态度的经典之作。稍早佛罗伦萨曾出现讨论艺术家生平的著作——当然中国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有了——而整个欧洲艺术理论中也贯穿着一脉“画如其人”的观念。但是这些观念在欧洲并未像中国那样在画坛上发生实际的影响,西方也未曾有过明显的“业余画派”。
中国的文人画家及其交游的圈子,通常都兼具鉴赏家、收藏家的身份,由他们的品鉴角度及上述的一些信念所发展出来的几种绘画,在手法上看起来常常像初学乍练,带点笨拙,起码和职业画家与院画家的洗练精到比较起来是如此。文人画家所作的通常是水墨画,或者只是敷上一些淡彩(但是复古风格除外,复古风格的绘画用色较为鲜明,这是由模仿或影射古代的绘画形式而来的,与一般色彩的写生功能略有差别)。再者,这些绘画不管是技艺生疏或是刻意避开流俗,若以物象外表的真实感来要求,通常不具有说服力;基本上他们画的是一个内在世界。在宋代大师笔下,特别是十一、十二世纪,中国绘画的写实风格这一面,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稍后数百年中,画风的发展方向渐渐远离写实风格,这是与宋代的写实成就有所关联的,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刻意地“不求形似”。当实际的纸上绘画真的不求形似了,同时的绘画理论就从旁推波助澜起来。
文人画的特征此处暂不详论,我们将这些特征及其他论题留待与相关的个别画家和画作一起呈现;目前,我们必须先观察一下元代画家的历史与社会背景。
第三节 元代的读书人
蒙古人当政后便了解到,保存汉人行政系统的精华并在朝中采用干练的汉人,有种种优点。元朝的开国之君忽必烈入主中原后,在位达十五年之久,一心一意想学汉人当个有文化的皇帝,延请了一些硕学大儒到北京来。但是他只建立了一套汉人文官制度的空壳子,其实内里完全是蒙古人在中原以外各汗国实施的军事化建制。
无论在中央或地方,政府官员一律行双轨制,有执掌军权的蒙古人或色目人,佐以管理文人政府的汉人。语言隔阂也造成沟通的障碍,忽必烈本人从来无法直接和他的汉人属下对话。应召食蒙古人之禄的汉人为数甚少;对大部分的读书人而言,在宋朝他们可以按部就班地升迁,但是在元朝便困难重重了。新王朝一开始就设下的社会阶级,决定了晋升的渠道,其中蒙古人是第一等,次一等是来到中原辅助蒙古人的外邦人。汉人居于最低等;甚至等下又有区别,而东南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所谓的江南地区)曾经是南宋故都所在,此地的汉人更受歧视,部分是因为他们对前朝依然忠心耿耿。江南地带不仅风光明媚、气候宜人,而且富甲全国又兼人文荟萃。蒙古人统治之下,这里的精英分子多半仕途坎坷。元代初期的社会据说分成“十等”,儒者在伶人(包括娼妓)之下,仅仅高于乞丐,排在第九,不管是否确有其事,或者只是失意文人的嘲谑,这些原本该是官僚体系中坚分子的人,在元朝的确是遭受严重的歧视。科举考试在元代一开始便被废除了,直到1315年才恢复。但即使恢复,江南地区的汉人仍然不易晋身仕途,因为考试对他们有诸多刁难,且名额有限。既然无法当官,有些人便退而求其次当个小吏,一旦破格擢用还是可以跻身官僚行列;但是升迁比登天还难,俸禄也少得可怜。
除了以上所说的障碍之外,视变节降敌为奇耻大辱,这种心结也使得大部分的知识阶层迟迟不愿加入新朝。比较幸运的人可以靠持有土地或变卖家产维生;其他人只有教书、行医或算命。有一些人知名度够,便可以文人或作家的身份谋职,尤其是到了元代末期;他们通常隶属于职业公会“书会”,写作墓志铭和序言之类来赚取润笔费,不然就编剧本。这些“处士”行业有异,却在江南地区共同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在这里传统的价值得以保存,过去的种种还受敬重。在这个世界,虽然无法完全摆脱不利的外在环境,但心灵是逍遥自在的,读书人可以把自己的人际关系只局限在一群意气相投的朋友之间;他们可以借着诗笔、书法和画艺,在这个圈子中或是在历史上拥有一些地位,甚至是名声。
第四节 遗民
蒙古人夺权之后,专制的统治使此起彼落的抗暴运动变得徒劳无功,直到十四世纪中叶才有大规模的叛变。是故,在元代早期,士人拒绝臣服蒙古人,跟任何公开对前宋表达忠贞的举动一样,可能只是出于守节之念,没有实际的目标可言。但是有很多人既不想接受蒙古人召举,也不愿隐藏对蒙古人的讥讽。这批人有的曾在宋朝为官,有的曾在动荡的年代奋力作战,要不就是曾经义愤填膺立誓不事二主。他们即是所谓的“遗民”。这些遗民离群索居,有时候转向宗教找寄托,泰半生活贫困,常聚会赋诗,隐喻故国之思。因为苦于没有有效的抵抗手段,促使他们采取一些象征性的举动,譬如坐卧不朝北(蒙古首都的方向)。有少数传世的绘画中也可以见到类似的象征手法。
You may also be interested in the following product(s)
-

XPf003 rice paper fan
£7.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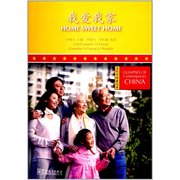


 Facebook
Facebook Twitter
Twitter Pinterest
Pinterest Google +
Goo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