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青岛出版社,青岛出版集团; 第1版 (2016年1月1日)
- 平装: 262页
- 语种: 简体中文
- 开本: 32
- ISBN: 9787555234340, 7555234343
- 条形码: 9787555234340
- 商品尺寸: 20.6 x 14.8 x 1.6 cm
- 商品重量: 399 g
- 品牌: 青岛出版社
Details
基本信息
编辑推荐
片山恭一代表作《在世界中心呼唤爱》
狂销东瀛350万册
你多久没被感动了?
暖心疗伤力作
作者简介
片山恭一 日本著名作家。 1964年生于日本爱媛县,九州大学农学系农业经济学专业毕业。二十二三岁开始创作小说。代表作有《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世界在你不知道的地方运转》《留下静的鸟儿》等。
目录
001 第一章
063 第二章
129 第三章
195 第四章
序言
珍惜﹃最后开的花﹄•••
文学的使命,一是直面现实,二是拯救现实。拯救现实,就是要找回现实中流失的东西。无须说,作为现实,我们生活的物质版图正急剧扩张。你可以坐德国的车、嚼美国的牛排、吃巴西的水果。只要你愿意,甚至可以“哈啰”一声随时打电话给布什父子。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心灵疆土却越来越瘠薄,越来越萎缩,以致除了自己几乎养不了也装不下第二个人。换言之,爱这一最可宝贵的水土正在迅速流失。相比之下,不少中国作家似乎更有直面现实的勇气,而日本当代作家片山恭一宁愿致力于填补水土流失造成的空缺,致力于对现实的拯救—— 呼唤爱,呼唤善,呼唤悲悯。
他的那部《在世界中心呼唤爱》无疑是这方面一个璀璨的结晶,和同名电影一起在日本创造了销量奇迹和票房神话。但片山恭一并未就此止步,而把在“呼唤爱”中意犹未尽的部分不断扩衍和深化,终于在去年推出又一部力作《最后开的花》。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已不再是“呼唤爱”中的毛头小子,而是成长为一家证券公司年富力强的基金经理,一个天天同钱打交道的股市操盘手。而且是出类拔萃的高手,以丰富的经验和准确的判断在波谲云诡的股市上赚得钵盈盆满,深得公司的器重。他自己也得到了构成世俗享乐的所有要素:高档公寓、高档家具、高档西装,出入高档餐馆酒吧,连离婚后结识的女友也是高档白领。这期间他偶然见到了十几年未见的大学女同学由希。由希身患先天性心脏病。重逢之初还能生活自理,也能和永江一起外出旅行。但病情的发展从未停止,绝无好转的可能。五年后,由希几乎卧床不起,甚至住院抢救,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然而就在此时,永江断然做出一个决定:辞去基金经理工作,断绝同女友的往来,即刻同由希结婚,陪她走完所剩无多的生命旅程……
这里有两个背景值得注意。一个是永江同波佐间的交往。波佐间同为永江的大学同学,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建筑公司的副总经理。他为了生男孩儿继承这家由祖父创办的公司老总职位而采取了胚胎基因诊断方法,不料生下来的男孩儿却有先天性情感缺陷。波佐间因此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决心跳崖自杀。永江随后进山寻找。永江在同波佐间交往的过程中、尤其在山中相遇后,两人对“9•11”事件后的世界形势和金融体制进行了猛烈抨击。如认为“和平”时下已沦为美国军事机器生产的“商品”,沦为“极其注重实利且浑身血污的东西”;认为“所谓全球化,无非是力图在货币这一超宗教之下对世界进行重组的运动”;认为与胚胎移植相关的基因工程已成为股票投资商们趋之若鹜的“实质上把人商品化”的商业活动。这一背景充满张力,字字句句,掷地有声。另一背景则是永江对自己同由希一起经历的点点滴滴的往事回忆。静静的夕晖,柔柔的晚风,轻轻的话语,伴随着淡淡的哀愁、绵绵的情思,时间在其间缓缓地流逝。
不难看出,正是这可谓一硬一软的两个背景使得主人公异乎寻常的纯爱有了质感,有了说服力。一个让主人公痛感灵魂的操守和生命的尊严正在遭受“世界的劫掠”;一个让他觉得只有由希、只有同由希的关系才能使自己避开“世界的劫掠”,使灵魂得到净化和救赎。从中,我们既看到了纯爱的依据,又看到了纯爱的价值和力量。
作者在小说出版不久对记者说:“由于物质和信息的介入,我们已无法真切地感受他者。他者完全成了景物、成了符号,于是社会变得一片荒凉”(《每日新闻》2005年7月17日)。为了让荒凉的社会和心灵的地表恢复植被,唯一的办法就是播散爱的种子。爱—— 近乎宗教感情的悲悯、对于他者设身处地的体察和不计功利的关怀,只有这种纯爱、博爱之情才能使我们的社会免于沦为不毛之地,使我们的灵魂不失贞操并得到超度。换言之,爱乃是人世间最后开的花。除了它,还有什么更值得我们珍惜的呢?
林少华
二零零六年元月六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瑞雪初霁满目银辉
文摘
1
人行道上,化妆化得富于挑逗性的女郎们身旁聚着身穿颜色发黑服装的男子。无论男女,全都无所事事,只是愣愣站着。女郎们大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不时擦肩而过的不知什么国籍的男子们用我听不明白的外国语交谈着。这座城市里莫名其妙的语言也多起来了—— 正这么想着,转而察觉他们口中的竟是日语。
星期五的夜晚。和几个同事在公司附近的餐馆喝完啤酒,又坐出租车一齐赶到六本木的酒吧。年轻的同事一杯接一杯喝着度数高的杜松子酒和苏格兰威士忌,简直像要把一星期来的心理压力用酒精冲个一干二净。醉得一塌糊涂的一个喝的过程中起身吐了一次。见他折回时脸色苍白,我为他要了一杯葡萄柚汁。他一口气喝干,紧接着要了一杯戈登。喂喂……看来他已打定主意:哪怕多少让肝脏纤维化,今晚也要一醉方休。见他第二次跑进卫生间之后,手机响了。
十二点都过了,街上也还是人如潮涌。泡沫经济破灭后冷清一段时间的这座城市,近几年又恢复了活力。不过,这只是表面上的。公司接待性活动减少,孩子们涌上成年人的街头。一个染发的年轻男子盘腿坐在人行道上,一边弹着吉他一边胡乱唱着什么。几个高中生模样的女孩蹲在大楼背后打手机。走过一个用萨克斯管吹奏《怀念乔治亚》(Georgia on my Mind)的蓄胡男子身旁,沿狭窄的小路往右一拐,来到人少些的地段。这一带人也好路也好都格外脏兮兮的。暖烘烘的风吹来,路上扔的纸屑随风起舞。
走上大路拦出租车。大概失火了,路面有警车和消防车的云梯,通往涩谷的路车来人往混乱不堪,很难拦住出租车。于是分开人墙,往稍离开些的地方走去。看热闹的人一齐往高楼顶上仰望。看情形好像有人要跳楼自杀,混乱由此而来。围观的人像看烟花一般,或骂骂咧咧或大声起哄,七嘴八舌喋喋不休。顺他们的视线不经意地看去,原来楼顶边缘站一个身穿泛白衣服的男子。
走了一段路,好歹拦住一辆出租车钻了进去。车内一股烟味儿。告以目的地,闭上眼睛,忽然有点儿想吐。为了冲淡呕感,我让意识集中在由希的身体状况上面。打来电话的是她的母亲,说是从医院打的,随即简单讲了女儿身上发生的事情。这位平时蛮刚强的母亲最后竟呜咽起来。
“消防车出动了,”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着我说,“失火?”
“像是跳楼自杀。”我懒懒地回答。
“跳下去了?”
“不,还没有。”
“是吗。”
交谈中断片刻。我一边怅然注视车窗外流动的街头景致,一边思忖刚才那个志愿自杀的人。那个人怎么样了呢?那般众目睽睽之下,说不定反倒跳不成了。下面围观人的起哄声仍执拗地留在耳底。
“人多大年纪?”司机再次问。
“脸没看清。”
“男的,是吧?”
“公司职员模样。”
“说不定被裁员裁掉了。”
“也可能醉酗酗懒得拦出租车了。”
司机没笑,我也无意逗他笑,只希望他闭上嘴开车。但不知是有意还是迟钝,他不想闭嘴。
“干这个之前,我是管裁员的。”他径自说起这个来,“在建筑公司人事部来着。”
我没有搭腔,把司机话当耳旁风。他以从容不迫的语气继续说下去。说泡沫经济破灭后,公司的订单当即一落千丈。结算情况不妙,连日开会,决定以多给退职金为条件征集二百名左右退职志愿者。他的任务是负责说服不愿退职的人。
“我列举数字说明严峻的现状,没使用辞退这一字眼,只说请求配合,或希望为年轻人着想等等。都是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心里不好受啊!”
我很厌烦司机的饶舌。对素不相识的客人说这个,到底什么用心?是想引起对方的共鸣,还是打算进行精神赎罪呢?看计程表旁边贴的名片式照片,估计年纪在五十五上下。
“当时使用的设想问答集的最后一项是:那么你是什么打算呢?”说到这里,他催促似的看着后视镜。
“回答呢?”我随便问了一句。
“走也地狱,留也地狱。”
我差点儿笑出。
“有道理。”我没有笑。
“但实际上没有人这么问。”司机以深有所感的语气继续道,“我是幸运的,因为大家尽管很不好受,但最后都予以配合了。这样,在没有发生什么争吵的情况下,两年左右就凑足了所需要的退职志愿者。”
车在六本木大街行驶。
“可是在完成目标舒一口气的同时,我觉得自己心里好像开了个空洞。”看来他非要把话说完不可,“设想问答集的那句提问就像打往心口窝的重拳躲闪不开—— ‘那么,你是什么打算呢?’”
“辞职了?”
“嗯,辞职干起了这个。”
大概总算满足了,司机安静下来。我闭目合眼,任车摇晃自己。我什么也不想,惟愿这么睡过去。
“去正门吗?”
问得我睁开眼睛,以大梦初醒的感觉环视四周。我一边从夹克内侧的口袋掏钱夹一边说:
“去夜间门诊那边。”
司机伸手拿过停车票后,拦车杆提了起来。
“这个时间还探病?”司机找回零钱,恍然大悟似的问了一句。
2
由希身上似乎发生了下面这样的事情。晚上十一点左右,她在自己房间床上睡着了。虽说一天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床上过,但也还有起床有就寝的。她尽可能中规中矩地保持白天和黑夜的区别。睡着大约一个小时后,强烈的胸痛使她醒了过来,向睡在隔壁的母亲求救,父母起来时她已陷入呼吸困难之中。父亲叫救护车时间里,嘴唇四周出现了青斑。拉到医院后马上输氧确保呼吸。但呼吸困难未得到改善,甚至出现意识障碍,处于危险状态。于是紧急往鼻腔插入气管,用人工呼吸机帮助呼吸,得以暂且脱离危险。
由希的父亲原封不动转达医生的说明。父母都很疲劳和憔悴,但因为事态在某种程度上已有所预料,看上去没有过于惊慌失措。
“能会面吗?”我问。
“求求看。”父亲说,“估计睡着了。”
我们跟着护士走进集中诊疗室。一排有几个用布帘隔开的房间,其中一个躺着由希。床边围着很多器械,几乎所有器械都伸出透明的或分色的软管连着她的身体。监控心跳次数的显示屏发出电子声。也有泵类刺耳的声响。此外还有不知从哪里发出的“嗞嗞”声。我摸了摸她放在床上的手。凉凉的,肤色也不好。碰了碰指甲,但没有反应。我站在床边,持续望着闭目合眼的由希。一会儿,护士返回,催我们离开集中诊疗室。
坐在长椅一端的父亲呆呆望着漆布地板。母亲躺在沙发上闭起眼睛。感觉上两人小了不少。去卫生间洗手时随意看了一眼镜子里自己的脸。我比由希的父母憔悴得多,胡楂黑乎乎的,眼圈多少陷了下去。由于没洗澡,头发油腻腻的。而且睡眠不足弄得脸色不好,由于饮酒过度,惟独双颊不自然地发红。若是韦思 ,很可能以这张脸为模特画一幅杰作。
看表,快后半夜两点了。我在自动售货机里买了纸杯装的咖啡,坐在休息室长椅上喝着。我回想和由希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那是上个星期六。
那天较晚的时候,我去了她位于柿木坂的家。被留下吃晚饭,连同她父母一起围在桌旁。多少喝了点酒,快到八点还在由希房间里磨磨蹭蹭。房间面对南面的庭院。房子相当旧,但窗是铝合金的。放着小书架,形成她单独使用的小图书室。大多是诗集、随笔集、游记类的书。最下面一格摆着几本大号影集,差不多全是以自然为对象的风景照。书架旁边放着她上小学时开始用的旧书桌。我就坐在桌前椅子上。
“近来做了个梦。”她忽然想起似的说,“梦见你永江了。”
“怕是好梦。”
“地点弄不大清,大约是大学校园里的一个角落,也就那样的地方。好像有个水池或喷水池什么的。你拿一条芦苇样的植物出现在那里,问我那叫什么名字,我说叫物种起源。”
我不由得笑了。
“何苦出来达尔文呢?”
“不知道。不过梦留下很深印象。”
“下次出现时,拿个地道些的东西。”
说梦到此为止。我从书架里拿起一本诗集,目光落在随手翻开的一页的诗句上面:
漫长岁月里我和你朝夕相伴
而今我们即将各自扬帆
为了重逢的那一天
正要往下看,由希唐突地抛出话题:
“高中古文课学过《枕草子》吧?”
我从打开的书页抬起头。
“现在还时不时想起菊花移香那一段。”
“讲的什么?”我合上书问。
“旧历九月九日是菊花节吧,在那前一天夜里把棉布盖在菊花上面沾得夜露,再用移有菊花香的棉布擦身—— 好像有这么一种风习。”
“《枕草子》是平安朝 的吧?”
“古人够细心的了。”
“风流地方也不是没有吧?”我说出另一种感想。
“我想那些人肯定很敏感细腻,都能玩味菊花淡淡的移香。”由希仍好像放不下古人那份细心。
“啊,现在用的倒大多是足以把人熏昏的香气。”我附和道。
不料由希不知是开玩笑还是当真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我若在菊花开的时候死了,你用菊花的移香给我擦身可好?”
“记住就是。”我轻轻应道。
交谈中断,房间里的静寂分外明显。房子位于从道路稍拐进些的地方,几乎没有车辆往来。过了一会儿,由希以仿佛自言自语的口气说:
“每年一到夏天,我就觉得自己活不到秋凉的时候,不知今年怎么样。”
我默然。
“过完这个夏天,父亲可能离开现在这家公司。”她继续道,“不过好像打算另找工作,想在能干的时候多干些,尽可能多留一点儿存款,尽管晓得我要先去那个世界。”
一直坐着的我从椅子立起,在她躺着的床头轻轻坐下,顺势拿起她的手。
“说得好心虚啊!”
由希伏下眼睛。少顷,老实说她近来有些突然透不过气。
“原以为不过是轻微发作,但后来一个劲儿担忧若剧烈发作可如何是好,担忧得晚上几乎睡不着。”
“跟父母说了?”
“没有。”她微微摇头,“说了,肯定提出睡在这房间里。那一来,母亲就休息不好了。本来为我操劳得够呛了,晚上时间再搭上,母亲要垮掉的。上年纪了,原本心脏就不好……”
天亮的时候护士来叫。我们战战兢兢跟在她身后走去。由希身上仍用着硬管和软管同器械连在一起,但眼睛睁开了。看见我,想做出笑容,但只是脸颊松了松,再次闭上眼睛。我拿起她的手。她已没了回握的气力。觉得如果用力过大,很可能把她整个人弄坏。
3
由希和我在大学里由同一教授指导。那位教授退休时,在城内一家宾馆举行了纪念晚会。会后,不少与会者接着去喝第二场。而我因为第二天要去国外出差,所以提前离开一步。她在出租车站那里。等车的人很多,看样子要等些时间。站着说话当中,得知两人回去的方向相同。我问她去宾馆会客厅喝杯茶如何。反正回去同乘一辆出租车,把她送到家即可。
我察觉自己比平时话多。我讲起几天前刚看的电影。是吉姆•谢里登的新作,主演是丹尼埃尔•D.刘易斯。舞台是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男主人公原是IRA 活动家,因实施恐怖性爆炸嫌疑入狱十四年,已刑满出狱。由于现在洗手不干,组织当然心生不快。所以返回原来城市是有危险的。他所以冒险返回,一是为了继续参加拳击比赛,二是为了同恋人相会。对方已经结婚生子,丈夫同样是IRA活动家,被关在监狱没出来。
“在IRA内部,服刑者的妻子作为斗争的象征具有特殊意义。有义务一边守护家庭一边在精神上支撑狱中的丈夫,放荡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就连有男人以眼神挑逗,组织的成员都要当即发出威胁。何况男主人公对组织来说等于叛徒。周围人都晓得两人曾是一对恋人。其实相隔十四年相见也没办法好好交谈,因为若被人瞧见传出去,就会有生命危险。”
“但两人还是相互吸引。”
“就是所谓犯禁的恋情。”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十四年前的恋人重逢时也还会相互吸引?”
“大概会的。”
“无动于衷的可能性也有的吧?”
“因为两人都一直思念对方。”
“不过实际相见,形同路人也有可能。”
“你是说时间会改变人?”
“嗯,双双改变。”由希不无悲戚地说,“结果,十四年前站在同一位置的两个人,现在说不定离得像英国教会和罗马天主教那么远。”
“那可就成不了电影喽!”
“的确成不了电影啊。”她笑了。
“不过相反的情况也有。”我说,“十四年前天各一方的两个人此时正在同一休息厅一起喝茶—— 我们成为电影。”
说来也怪,大学时代我们并不特别要好。我有相处的女孩,由希在同一课堂上的女生中间总的说来也不显眼。
“头发长得很不一般,”她眯细眼睛说,“胡须也够长的吧?”
“记得蛮清楚嘛。”
“那是的,人家喜欢你永江来着。”
语气像谈天气似的。我不知怎么应对才好,便向旁边走过的女服务生要了瓶啤酒,以便再琢磨一下她口中“来着”这个过去时的含义。我把啤酒倒进两个杯子,讲起毕业以来的情况:曾在银行工作,眼下的工作,结婚和离婚的原委……如此讲述自己的经历还是头一遭。可能是十几年没见的关系,也许因了对方始料未及的表白,或者仅仅心血来潮也未可知。她默默倾听我的话,除了偶尔附和一声,几乎没有插话。
我说完之后,她接着说了起来。字斟句酌,声音十分平静。说的过程中有时夹带长久的沉默。若是电话咨询,即使对方说出“下一位”也是奈何不得的—— 便是这么长的沉默。然而两人都不觉得别扭。倾听由希讲述,觉得就好像独自走在寂静的森林。她日常生活中流淌的时间同我度过的时间似乎截然不同。
“在新宿一起看电影来着,记得?”她道出意外的事来。
“和我?”
“不记得了?”
记忆中完全没有。
“看的什么?”
“忘了。”
“那么就是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电影。”
她继续下文,语气仿佛在说那个怎么都无所谓。
“有条连接东口和西口的地下通道吧?那时候东口旁边那个地角还是空地,或者像是个停车场。倒是铺着水泥,但这里那里不是有裂缝就是碎了,露出下面的土,长着很多杂草。”
我当即明白她说的是哪里。
“长着像木莓那样的野草,结着很多小果果。蹲下来用手一碰,你说那是Cloudberry 。”
她还是记错人了。
“真的是我?”
“欺负人!”
“不不。可这……”
此人同自己果真有相同的过去不成?理应共同拥有的过去,实际上说不定是别的东西。人与人所能共同拥有的仅仅是现在,若对这点有所怠慢,心势必分离,一如往日的妻子和我经历过的。
“回来路上不是还在涩谷喝茶了么?”她言之凿凿地说,“店里黑得要命,脏得要死,吵得不行。放着鲍勃•迪伦的唱片。你说他的歌词很难懂,还说再次和孟菲斯•布鲁斯一起被关进大型移动住宅到底什么意思。”
她口中说出的情景简直像昨天的事一样鲜明。
“这回你还装糊涂?”
我提起音乐话题来逃避她的追问。
“六十年代迪伦的歌词,有说法认为几乎全是毒品。我一边翻开尤金•兰迪的《美国俗语辞典》同朋友各持一词争执不下,一边解释歌词来着。”
“和一个吸大麻的女孩之间有风言风语,知道?”
“我?”
今晚全是令人吃惊的事,我心想。
“真吸来着?”
“怎么可能呢!”
她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
“那么说,我想起来了。”我以接受刑警审问的嫌疑人那样的心情说道,“有人说用英日辞典的纸页卷红茶叶吸有一股大麻味儿。一边吸呛嗓子的烟一边听迪伦和‘斯通兄弟’。但吸真正大麻的家伙,我身边应该没有。就连有没有人见过真正的大麻……不管怎么说,我那本英日辞典确实丢一页坏一页的。X啦Z啦,撕扯的是不怎么查阅的部分,这点倒也够可爱的。”
在休息厅坐了一个来小时。出门时下起了雨。我用出租车把她送到家。车上几乎没说话。
“今晚太谢谢了!”车停在她家门前时她说道。
“偶尔打个电话可以的?”我随便问了一句。
“嗯。”她微微一笑,“基本在家东倒西歪,有电话来我会高兴的。”
我开始照自己说的做,或许该说做过头了。每月往她家打几个电话。就像初中生打长电话一样,没头没脑东拉西扯。说的几乎全是我,她大多当听众。尽管如此,她的生活场景也还是从谈话中一点点浮现出来:养一条杂种狗,弹钢琴,喜欢野生紫罗兰。由希独身,去她家里应该不碍事,但我没有介入她的生活,而代之以偶尔约她出去。美术馆举办有意思的展览,两人就在平日上午等人比较稀少的时间段前去观看。音乐会也去了,还开车往远处去了几次。秋天去看红叶,冬天去看雪景。
这些小小的乐趣正一点点失去。她的病是先天性的。心脏很难往肺部送血,致使短时间出现呼吸困难。病情一步步发展,最终只能采取同时移植心肺的治疗方法。国内不大可能做这种移植手术,而在美国或澳大利亚做又费用太高。即使费用能够筹措,也未必能找到器官捐献者。就算碰巧找到了,手术也不一定成功。
病情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点点榨取由希的生命。她必须随着病情的发展适应一个又一个新阶段。刚适应就再次被榨取掉,绝对不会好转。即使看上去暂时控制住了,病情也还是暗中发展。
我们重逢的时候,由希还可以歇歇停停地料理家务。可是病情缓慢而又执著地向前推进。外出路上必须频繁地站住休息。又不能站太久,所以家务差不多全交给了母亲。此外以前能做的事也一点点做不成了,例如出去遛狗、去附近商店买日用品、上下楼梯等等。狗由一个熟人领养了。由于不能长时间坐,钢琴也弹不成了。不觉之间,一天中的多半时间要在床上度过了。
上个月还能做的事在这个月却做不到了,这将是怎样一种心情呢?莫非类似以“快捷键”体验衰老?而由希却以正常的精神状态忍耐这一遭遇,在我看来她已超越令人惊诧的范围,成了不可思议的存在。除了忍耐自由被剥夺的苦难,最近又增加了呼吸困难等肉体痛苦,并且没有减轻的希望。痛苦像熵一样有增无减,等到承担不了的时候,她势必死去,只要时间之箭不改变射向。而那一时刻已为时不远。
You may also be interested in the following product(s)
-

长生殿(舞台本)(汉英对照)
£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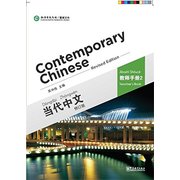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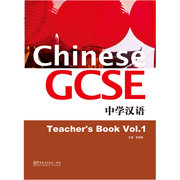



 Facebook
Facebook Twitter
Twitter Pinterest
Pinterest Google +
Goo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