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13年1月1日)
- 外文书名: Art in China
- 丛书名: 牛津艺术史
- 平装: 265页
- 语种: 简体中文
- 开本: 16
- ISBN: 7208108072, 9787208108073
- 条形码: 9787208108073
- 商品尺寸: 24.2 x 17 x 1.4 cm
- 商品重量: 481 g
- 品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Details
基本信息
编辑推荐
《牛津艺术史:中国艺术》编辑推荐:“牛津艺术史”中文版最新品种:牛津艺术史——西方当代最权威的艺术史丛书,由英语世界顶尖学者撰著,采用开放式的出版理念,已出版三十余种。每种配有百幅以上的全彩精美图版,用前沿观点与新颖材料阐述艺术史核心问题,被誉为“通向21世纪艺术史的大门”。
中文版一辑特邀美术史家、中央美术学院易英教授主持编选翻译工作,精选了国内艺术史研究界当下最需要的十种专著,侧重于构建西方艺术史的核心脉络,并兼顾富于当代性的新选题。
中国美术史国际权威学者柯律格经典著作,以最前沿的学术观念盘整中国艺术史脉络。
国内外一流美术院校学者:杰西卡•罗森(牛津大学副校长,墨顿学院院长)、朱莉亚•穆雷(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曹意强(中国美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等人郑重推荐!
名人推荐
《中国艺术》是一次对中国艺术的全新审视……生动而晓畅。
——杰西卡•罗森(牛津大学副校长、莫顿学院院长)
全书论述清晰,不时冒出激动人心的见解,将最新的考古发现和学界的大量研究成果巧妙嵌合,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茱莉亚•穆雷(威斯康辛大学教授)
这本书是对传统艺术史的巨大挑战,文辞优美,充满智慧。
——曹意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
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柯律格(Craig Clunas) 译者:刘颖
柯律格(Craig Clunas),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系讲座教授,中国美术史及物质文明史重要学者。曾任职于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远东部,长期负责中国艺术品研究及策展工作。2006年,因在中国文化和艺术史研究领域中的成就和贡献,被提名为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著有《长物志: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地位》《雅债:文徵明的社会性艺术》《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等。
刘颖,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现任教于成都大学美术学院,从事美术史教学和中国宗教美术研究。
牛津艺术史丛书中文版主编简介
易英,美术史家,艺术批评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美术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美术研究》杂志社社长、《世界美术》杂志主编。曾著译有《世界美术全集:西方20世纪美术》、《西方当代美术批评文选》等大量作品。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墓室艺术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前2500—前200年
第一帝国:公元前221—220年
北方和南方:220—589年
墓室雕塑:400—650年
第二章 宫廷艺术
唐至宋初:618—960年
北宋宫廷艺术:960—1127年
南宋宫廷艺术:1127—1279年
元代宫廷艺术:1279—1368年
明代宫廷艺术:1368—1644年
清初宫廷艺术:1644—1735年
乾隆时期:1736—1795年
晚清宫廷艺术:1796—1911年
第三章 寺观艺术
早期佛教艺术
佛教艺术:约450—约580年
隋(581—618)唐(618—906)的宗教艺术
北宋宗教艺术:960—1127年
南宋宗教艺术:1127—1279年
南宋僧人与文人
元代佛教艺术:1279—1368年
14—15世纪的宗教绘画
明代宗教艺术:1368—1644年
清代宗教艺术:1644—1911年
第四章 文人生活中的艺术
文人艺术——书法
北宋的艺术与理论
南宋(1127—1279)和元(1279—1368)
明:1368—1644年
董其昌的艺术和理论:1555—1636年
17世纪和明清转型
清:1644—1911年
19世纪
第五章 艺术市场
宋元时期:960—1368年
明(1368—1644):绘画
明(1368—1644):印刷
明(1368—1644):纺织品和手工艺品
晚明绘画中的业余与职业问题
清:1644—1911年
版画与透视图
19世纪的上海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艺术
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中国艺术
注释
插图一览表
参考文献
大事记
索引
序言
导言
“中国艺术”是新创造的词汇,它出现的时间不足百年。虽然本书中出现的纺织品、书法、绘画、雕塑、陶器以及其他艺术品来自5000年的漫长时代,但是按材质进行分类并命名为“中国艺术”仅是非常短暂的历史。尽管中国有漫长而富有经验的书写艺术的传统,世世代代贵族文人爱好收藏、陈列以及消费艺术品,但是在19世纪以前,无人将这些物品视为同一领域的组成部分。确切说来,“中国艺术”一词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和北美洲。“中国艺术”在西方是作为与纯粹的“艺术”对比研究的对象而存在,“艺术”实际上是欧洲传统,并且扩展到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伦敦“国家画廊”
(National Gallery)和华盛顿“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的名称隐含了包容性的主张,然而它们没有接纳来自中国的艺术品。
19世纪创造的“中国艺术”一词使得描述一些器物的样式并判断它们的价值归属成为可能。这些描述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中国”本身。19世纪的德国思想家黑格尔视艺术为人类的精神,他的观点与东方学者的中国观点完全吻合,黑格尔认为它们的本质只有那些非中国人才能了解和描绘,由此而产生了书写“中国艺术”的特殊方法。它通常以牺牲变化为代价而强调连续性,以牺牲同一事物有争议的用途为代价而强调和谐性,以牺牲差异性为代价而强调必要的同质性。更确切地说,是强调中国与“西方艺术传统”的差异,而在中国实践领域里跨时空的差异性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可是,中国是一个地理疆域广阔的大国,跨越了多个气候地带和生态环境。在那里,社会和宗教的观念、统治精英的民族成分、政治权力的地理分布以及人口主要聚集区都曾经历过诸多的变化。
这本书有意取名为“艺术在中国”(Art in China),而不是“中国的艺术”(Chinese Art),因为它的书写不遵循任何既定的统一原则或要素,囊括了大范围的艺术作品,来自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材料以及完全不同的创作者、观者和使用背景。因为插图和文字的数量受到作者的精力、读者的耐心和出版的财力限制,所以选择哪些作品进入本书,或者放弃哪些作品至今仍是偶然的。“什么是中国艺术(art in China)?”这一问题可以转述成“是谁在何时将何物在历史上把它们称为中国艺术(art in China)?”如果本书不能完满地回答,那也是本书提出的问题之一。因为即便是快速地查阅已有的文献也会发现,任何关于“中国艺术”(Chinese art)的定义中都存在诸多的异常现象和内在矛盾。它永远都不能被理解为一个稳定的、不变的统一体,除非我们将编目者和他的立场纳入考虑当中,才能由此完全地接近它。例如,近一千年来中国文人定义的“艺术”(art)总是将书法放在第一位,然而西方的研究一般趋向于留给雕塑更多的空间而不是书法。雕塑在西方后文艺复兴(post-Renaissance)传统中就被确立为“美术”(ne art),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法国学者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22),开拓性著作《伟大的中国雕塑》(The Great Statuary of China)的作者,拒绝涉及中国的佛教雕塑(在所有的机构中收藏有大量的佛教雕塑),基于它“非真正中国”的理由,确切地说是来自印度的“外国”文化输入,它给那些他极度赞赏的纯粹本土作品带来了彻底的伤害。[1]
我在本书里有同样鲁莽的决定,如果受到读者的质疑是很寻常的事。例如,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没有涉及建筑物。本世纪之前,还没有关于作为中国美术(fine arts in china)之一部分的“建筑”(architecture)的论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关于建筑(buildings),没有如本书涉及的其他(同样是未理论化的[under-theorized])门类那样的美学思考。内容的选择和放弃受制于出版的版式,但是却不能用排版对内容取舍加以解释。
因此,读者不必认为书中列举的约120件作品是历史悠久的经典杰作的代表,或者是一张被认可的艺术珍品的目录。更准确地说它们代表了多样的与众不同的生活历史。一些作品早在制作的当时当地就被视为艺术品,并且在随后的记载中继续被认为是杰出的作品,一直延续到当下,而其他一些作品的艺术身份则是我们这个时代强加的。有一些作品恰好不属于传统而经典的“重要”艺术品,它们因未能符合品质需求的标准而在这类介绍性著作中面临着挑战。我选择它们的原则是作品可以支撑著作的背景,它们在中国从古至今都被视为艺术品。其中许多作品已经是英文类创新学术研究的主题,详细内容见注释和参考书目。它们仅仅是一个起点,不是不偏不倚的范例。本书论述了跨度巨大的中国艺术,其中大部分作品已经遗失,即便是这样,一本现代标准的参考书还列举了13000多名画家。[2]我曾经试图花些篇幅讲一下一件作品在它产生的时代是如何被明确地称为艺术品的,享有特权的书法和绘画在一定程度上的意义,但是我也意识到,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艺术”现在包括各种类别的材质,无法弄清楚它们的关系,而自觉的审美感受是主要的价值。这就证明了将世俗的和宗教的石雕都包括在内是正确的,除了能够建构起幸存的物质证据之外,事实上对它们的赞助人我们一无所知,对创作者也完全不了解。
需要简略说明本书的结构,因为它既不是完全按年代顺序也不是按主题编排,但我不需要觉得抱歉。没有参照框架是自然的。本书利用的支撑材料绝不比其他的著作更少或者更多。它站在自己的出发点利用背景材料,即创造和使用这些艺术品的社会和物质环境。关于这点的争议之一是,在中国艺术的研究中这一方面此前很少受到关注。事实上,在中国和西方的知识传统中,“艺术”和功能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有了相互独立的范畴。19世纪以来,一件艺术品不具有实用功能,或者被视为移除或者隐藏了功能的物品。
接下来的章节涉及墓室艺术遗迹、统治者的宫廷、举行宗教仪式的寺庙和祭坛、社会生活和上层社会的相互影响,以及市场理念等内容。我认为它们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许多作品可以在几个主题下进行讨论,实际上一些作品多次被提到。我会优先说明一件特定作品的意义的诠释是怎样随着时间而改变的。在本书中它作为“艺术品”出现,可能是一系列类型中最新的一个,其中每一个类型都代表一个主题。
文摘
插图:





第一章 墓室艺术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前2500—前200年
在不同的时期,多重的含义悄然隐含于中国的美术作品中,恰好可以从一件目前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玉圭里发现这种情形[图1]。石料呈乳黄色,因为年代久远而天然包含了一些灰色和赭色的物质,被磨制成梯形薄片,在较窄的一头有钻孔。精致的浅浮雕部分,一面雕刻正在跳跃捕食的鸟,图像轮廓清晰,另一面则是一张神秘的程式化的脸,有突出的双眼。据考古发现的证据,我们推测,这件作品大概制作于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为龙山文化(约前3000—约前1700)的产物,在此时期龙山文化在距离黄河出海口不远的今山东省的位置繁荣起来。工匠在金属使用之前制
作了它,而玉石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制作工具和兵器的材料,也是在已经确立的阶级社会中一些人的身份显赫于他人的证明。玉圭上有纪年为1786年的铭文,是一位中国帝王的题字,在他大量的古代藏品中,在那年此物证明了它自身的存在。他给玉圭两面的装饰提供了奇特的解释,理解为鹰和熊的象征,是给勇者的一种古老奖励,并将玉圭归入中国古代最早的两个历史王朝,商(约前1500—约前1050)或周(约前1050—前256)。
这很容易和“中国人好古”(the Chinese love of antiquity)联系起来,它描绘了一些人以某种方式沉浸于阐释他们自己长久而辉煌的过去,把过去想像成完整一体的,其他文明不能与之匹敌。我更想强调这件古代作品(实际上比题字的帝王所确定的年代更为古老)的创造性挪用,它插入到一个实际的新语境中,也就是皇家藏品中。而且皇帝声称的正统性是通过使用权力的古代象征物来实现,在这点上与许多其他的文化系使用有威望的建筑形制、艺术作品或收集以往的财宝去支持眼前计划的行为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实际上玉圭出现在本书中作为“中国艺术”的一个实例,它所在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同样表现了玉圭铭文装饰的新语境、新含义,想必与乾隆皇帝富有想像力的流露一样。我们可以尝试阐释这件作品最初是怎样被构想的,但是无从了解它“真正的意义”。
公元前6000—前5000年,玉石,或恰好是软玉,首先被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系文化所使用。它是硬度极大的一种矿石,无法用金属刀片切割,但是可以用研磨砂,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切割和钻孔,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工艺。因此,在很早的时期,它便与权力结合在一起:世俗的权力,财力之上的控制意识,以及用于精神性权力的扩张。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人们利用附近的石材制作出高水平的玉器,中国的某地那时已经拥有长久而独特的玉器制作历史。我认为,如果说这片疆域内的所有文化都属于“中国人”,或者说是今天中国人的祖先,这种说法仍是一种推断,有一种政治性的假设色彩。他们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记载,虽然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用几千年后写下的中国文字去阐释如此久远的作品的含义及用途是极度可疑的行为。正如图中的圭,这是一件用于特定场合的“祭祀玉器”。它是在中国新石器墓葬中发现的大量的式样之一,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用途。或许这类与众不同的器物是在更早的偏南方的良渚文化(约前3300—约前2250)遗址中发现的。这里出土了一些平的盘状物,尺寸变得相当大,以及分割成段的中空筒状物,在转角处刻有人类形象,是这个地方最早的人类图画之一。这些不能和日常工具对应,有人指出它们可能表示“其他”的王国,指向超越世俗的力量。它们出现在墓室中(墓室大约有100余件玉器)暗示与世间辨识身份地位的标志的某些联系,但是我们不能推测得更远。在晚些的中国礼仪性文献中有这些玉器的名字(现在圆盘状物称为璧,筒状物称为琮),同时解释了它们在天地崇拜中的功能。它们也是贵族阶层等
级秩序的标志。但是这些文本对新石器时代的环境的实用性确实很小。接受关于如此古老的器物阐释的有限性更为可取,而不是力图使物质文化的证据适应于(晚得多的)文字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在从事中国广阔范围的农业和其他地面活动的过程中,人们很可能不断地发现这些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它们通常被解释成具有重大意义的器物,是意义的载体。已经改变的是其真实的含义,尽管非权威的文字材料为其提供了神秘而且似乎无穷尽的迷人指南。
自公元前1000年初以来就未曾中断的文本记录,作为文化和政治的正统来源享有很高的威望,字里行间似乎容纳了中国早期历史进程的清晰画卷。首先出现的是许多独特的文化英雄般的统治者,像大禹一样的人类恩公,他制服了中国大河中难以驾驭的洪水,而其他人发明了文明生活的必须品(衣服、房屋、农业,最重要的是文字书写)。在历史进程中,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或统治家族是夏(传统的纪年为前2205—前1818),它被商王朝(前1500—前1050)所灭,之后周王朝(前1050—前256)又颠覆了商。在周的统治下,为了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相关的文献被记载下来。20世纪初对这些记述的疑虑广泛流传,直到发现商代晚期王室的首都安阳遗址,它们才重获新生。发现的刻辞里有商王询问神圣权力的事,商王的名字与那些现在被证实的古代历史材料的记载相符。安阳仍是惟一出土了大量用最早的中国语言文字记载刻辞的早期遗址,刻辞刻画在乌龟的外壳或者动物的骨头上,它们充当了从世俗之地进入神圣世界的入口。此外,此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上也有铭文。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开始使用青铜,铜和锡的合金制作器物,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成立时刻。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用这种贵金属制作容器和兵器,是由成群的技术熟练的工匠来完成,他们的技艺可能代代相传,这些展示了早期统治者及其家族可以调用的资源种类的扩张。美国学者罗伯特•贝格利(Robert Bagley)提出,约在公元前1500—前1300年[1],模制青铜制造工艺首先在中国北方平原发展起来,这片区域以及它的附属国享受着黄河水的灌溉。商代早期,政治权力从这里向南方扩展。安阳时代之始,公元前1300—前1000年,商王朝的政治势力削弱了,缩小到它的核心地区河南。南方的青铜器,通常是虎和象之类的动物形象,并不依赖于安阳,在相互影响的早期阶段南方适应了独立发展而区别于北方。
地理和文化上统一的早期中国,拥有强大而富裕的中心地位,它的影响向外扩展到相当大的区域,安阳遗址的发掘展现了它的盛况。1928年开始由国民政府出资,中国第一代专业考古学家实施了发掘。正是古代中国用可资利用的过去满足了全新的而又常常四分五裂的民国的需要。尤其是它支持了最早的文献中关于早期历史的叙述,它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渴望“现代性”与不舍抛弃几十个世纪的文字遗产之间的紧张状态。构成考古学组成部分的科学论述是“现代性”的表示。如今,一幅更异类的、迥然不同的、缺少民族纯正血统的古代中国画卷正围绕在发掘出的非同寻常的发现周围,考古发现揭示了确定无疑的古老文化及其复杂性,它远离人们从传统意义理解的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带。对很多人来说,多中心的古代中国对当前的需求更具有雄辩力,胜过古老叙述的大一统。
这些遗址中没有一个比四川成都附近的广汉三星堆更具有对权威记述的潜在破坏性。三星堆发现于1986年,它颠覆了之前所有的早期中国文化、考古以及艺术的模式。在这里,与商代安阳同时代的用泥土夯起的城墙之外,设置有两个祭祀坑。第一个年代在公元前1300—前1200年,第二个晚了几十年。在大量的被焚烧过的动物遗骸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金器、青铜器、玉器和陶器,它们的样式完全不为人知,现代人的眼睛见到的最壮观场景是第一个祭祀坑出土的一组与真人同样大小的青铜头像和高达262厘米的巨型单体青铜像[图2]。在工艺上,这些青铜像类似,甚至超过在安阳制造的所有器物,长期以来人们视安阳为“中国文明的摇篮”。然而,它们的美学标准有惊人的差异,许多学者第一次见到这些器物的反应是,他们看到的是“非中国”的。换句话说,它们看起来不是用于建构“中国式”观念的器物。此前人们不知道这个时期以如此规模表现人类形象,且不用说与众不同的庞大,以及广汉头像上凝视的双眼和线条分明的鼻梁,或者是绷紧的站立姿势,双臂塑造成正握着某件木质或象牙的器物,现在已经丢失。
没有文字记载提到这支文化繁荣的时代。我们不知道他们把自己想像成谁,或者他们与其他同时代的位于今天中国其他地区的王国之间的关系。他们确实与长江流域沿岸的青铜文化联系紧密,可能从那里引进了青铜器。我们不知道是怎样、在哪里,或者又是谁在使用广汉青铜像。这些祭祀坑既不是人类的墓葬,又不像在安阳发现的人殉坑。包括青铜铸造在内的运作规模和玉器制造暗示了统治者的权力与财富。他们不是以安阳为“核心”的“外围”的一部分,在研究其文化区别于安阳的方式当中(没有制造青铜容器和编钟,主要是人类形象),不必以商文化为标准而认为广汉文化偏离了这个标准,这点很重要。
在安阳,新的发掘极大地扩展和复杂化了商代的早期景象和文化。尤其是,它提供了非青铜和玉石的其他材质的器物的阐释,它们在最初的解读中占据了主导。涂上红色和黑色的灰泥墙碎片也被复原,它暗示在商代统治者的生活中,视觉文化环绕在他们周围。但是更多的证据仍然来自围绕在死者身边的陪葬品。1976年,商代王室贵妇妇好(武丁妻子)的墓室被发现,墓室未曾被盗,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年。除了依靠墓室中的陪葬品之外,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这位女性的身份和生活。墓室采用的是大型竖穴墓,可能修建有地面建筑保护它,为进行祭祀活动提供空间,并且在王室陵墓中宣告它的存在。陪葬品很丰富,有200多件青铜器,加上兵器和700余件祭祀玉器以及个人饰物。其中有件独特的象牙敞口杯[图3],雅致的凹形筒身镶嵌绿松石,这种样式和装饰与青铜器物有某种联系,但并不是直接复制其他任何已知的范例而来。青铜的耐久性正好将其置于所有从历史和现代的角度理解中国早期艺术的中心,但是这件敞口杯显然丢失了什么,应该是木质或其他容易腐烂的材料,它们的价值可能与主人的身份相符,那将永远无法为我们所知。青铜器是根据主人的不同身份成组制造,器物有相同的样式、不同的尺寸以及精心制作的装饰,在人们的观念里,它们不是单独的器物而是整套器物的组成部分,其使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用在王室典礼上,供奉祖先的祭祀中,以及葬礼场合中。单件的奢侈器物对拥有者来说可能承载了更多的特定意义,这件独特的敞口杯可能是外来物品。象牙在本地是难得之物(3000年前中国的气候更温和,大象生活在比今天更靠北的地方),而且绿松石也从遥远的地方进口。如此说来,它仅仅是妇好收藏的财富中众多的新奇物品之一,这些藏品还包括“古董”,特别是玉器,前文谈到的新石器文化的器物在她生活的时代已经很古老了,也有当时古代器物的仿制品。
敞口杯有鸟状的把手,并且装饰恐怖的兽面纹。这些是商代青铜器上最常见的母题之一,有时候被辨识为后来才被命名的“饕餮”,意思是像近几百年的语言中的一种“凶恶贪吃的野兽”。这些面部有角,一双凝视突出的眼睛,具有特色的是它有两部分,各朝两边水平伸展。释读此纹样和其他母题近年来在学者中成为再度兴盛的议题。有些学者主张,在我们几乎完全不了解的此时期的口头或文本文学作品和宗教仪式中,它可以被诠释为商代神话和文化的象征,它代表了发源于别处的某种信仰。他们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在结构主义中,完全不同的现象反映了意义的潜在结构),尝试以现存的青铜器的物证来重建这个信仰的体系。其他学者,因为与美术史传统的关系顺理成章地被理解为“形式主义”,他们认为越过物品本身特征的任何讨论都应该严厉排斥,只有铸造过程的工艺特征,以及风格发展的内在规律,跨越了物质证据本身才对此类及其他母题产生影响。虽然无需争辩这些母题都没有意义,但是有些学者倾向这样的观点,认为我们不可能从表面装饰的视觉特征去解读已经消失的信仰。因此,他们承认我们永远不可能明白像妇好一样的王室贵妇是怎样使诸如这件象牙容器之类的器物上的装饰纹样概念化,与之相对的是她会怎样考虑对这些器物的拥有的关于权力与威望的内涵。
商代青铜器大量被保存下来是因为它们被埋藏在许多男人和女人的墓室中。在被制造的时代它们主要用在祠庙的祭祀中,为王室祖先供奉食物。它们和主人埋葬在一起,为了他们自己在死后还能继续为更高层的权力者献祭,并且他们也转而成了祖先。器物是权力的证物,这在周以后突然成为了重点,周王朝是来自商王国西部的一支民族,它约在公元前1050年灭商。周王使用了这些青铜礼器,也必然使用金属铸造青铜器,作为奖励分配给他的拥护者。从这个时期开始,越来越多的事件在青铜器上以铸造铭文的方式记录下来。在此,青铜器与玉器、兵器以及战车配件没有任何区别,都是贵族生活方式的附属物,作为等级的承载体,通过家族继续传承其显贵。最早的青铜铭文强调了这些“重器”是要“子子孙孙永宝用”的事实。这样的铭文可能抄写了祭祀典礼中的惯用语,在祭祀中食物都奉献给祖先。周早期的铭文铸在容器里面,在使用时它们被覆盖,原因可能是他们打算在祖先眼前一样给活着的参与者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可以建立起商和周贵族怎样理解这些青铜器的事实,并且,对于它们是怎样铸造的,我们也可以谈论很多。制造者的名字彻底被忽略了。青铜器上从来不会记载工场组织里每位工匠的名字,虽然我们能够以类推的方法从后来的资料中指出是一群代代相传的专业工匠制造了它们,但是我们对此并不确定。考虑到青铜器的神圣性,以及在许多相似的文化背景下金属制造工匠的特殊身份,我们推测,那时可能有像祭司或者巫师这样的人物,他们能够促使器物成为统治者集中关切的重点,但是也没有任何资料记载。我们也不知道制造它们的工场是怎样的组织,例如,他们是否采用分工的某种形式,不同的工匠负责生产程序中的不同阶段。较容易理解的是早期青铜器制造经过了非常复杂的铸造程序。利用完工的容器制作阴模,分成几个部分,然后极为仔细地装配在一起(即便如此,金属制品上永恒的“合缝线”说明了合范结合的部位)。把一个泥芯放入模具中,熔化的金属灌入泥芯和外范之间。最后,拆除外范,锉掉多余的金属,器物就完成了。当还是全新时,商周青铜器应该是亮光闪闪,而没有现在已成为它们美感魅力之一部分的氧化铜绿锈。尽管从理论上来说这个程序提供了重新使用模范的可能性,但让人惊讶地是没有证据证明曾经这样做过。
商周青铜器在样式和装饰母题方面表现出的相似性,直到最近人们才明白,这些相似性掩盖了它们在使用方式上的显著差异,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使用者的理解方式不同。这实际上发展成约公元前900年发生的“礼制革命”(ritual revolution)。青铜器在装饰方面变得朴素,并且出现大量铭文(这时有时候铭文是刻在器物外),因为代替纹饰的清晰的文字同样是所有者权力与威望的重要标记。一些不同外形的青铜器完全失去了实用性。成组的青铜器仍然被埋入墓室中,但是它们变成了不同类别的储藏物,储藏的财宝,与人的葬礼无关,器物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不是特定的祭祀器物的一部分。图中的巨大青铜酒器[图4]是出土的最大的储藏财宝中的一件,1976年在陕西省扶风庄白发现了103件。埋藏坑里装满这个文官家族珍贵的祖传遗物,他们属于微史家族祖辛,约埋藏于公元前900—前800年,是为了保护它们远离当时政权不稳定带来的危险,此后未能再被发现。作为来自他们祖先祭坛的器物,这些藏品由一组现在还能使用的器物组成,还有一些对此家族有重要意义的更早的器物。这件酒器是件古董,铭文上说在周昭王十九年铸成,根据传统的纪年方法相当于大约公元前964—前962年。因此当它被埋葬时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它与令人敬畏的祖先联系在一起,所以被保存下来,除此之外,它纯粹审美范畴难以确定,当然并不意味着完全缺少这些方面的意识。有的青铜器明显比其他的制作更精美,更宏大,铭文繁多,装饰精良。人们差不多是这样理解它们,与合乎逻辑的意义相联系,在这样的辨识中我们有了艺术概念起源的必要条件。
当公元前一千年发展进程的考古报告日渐丰富,它为进一步将青铜器从宗教仪式中解脱出来提供了证据,因为它们反而与炫耀和奢侈消费的范畴联系起来。在中国以后的历史时期中,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向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的更替中,这些名称来自这一时期的编年史,是对周王中央集权的、神圣权力的尊崇逐渐衰微的表征,许多大小不同、相互对抗的诸侯国之间残酷而持久的政权冲突成为周的接替者。文化的竞争扩展到物质领域,许多地方王室的奢侈之风成为维护统治者的威望和在盟友与敌人面前保持脸面的方式之一。
这类王室文化的某些部分可以通过曾侯乙墓室中的内容来重建,那是在今天湖北省的一个小国家,曾侯约在公元前433年去世(侯,类似公爵或其他的头衔,所指相当于中国统治阶层的头衔)。他被埋葬在一个精心制造的木质彩绘棺椁中,陪葬了大量的奢侈品,有青铜器、兵器、一套青铜编钟,以及乐器和木漆家具之类的物品,还有金器与玉器。这些用贵金属制作的幸存物品更清楚地展现了青铜怎样适应了整个文化系统,它仍然是此系文化的重要金属,然而它们仅仅是奢侈器物中的一类,而不是和商周时期一样,是文化意义和威望的独特权力承载物。图中器物来自曾侯乙的陪葬品,是一套青铜尊和盘,均为技艺纯熟的铸造品,它的表面布满扭曲的龙和虎,装饰在排列紧密的卷形饰物中[图5]。这是一种繁复之美(aesthetic of excess),“越多越好”(more is more),有些部分可能采用“失蜡”铸造工艺制作。这是制作小型立体金属器物较为实用的方法,复杂和精确的雕刻使得传统的组合泥范很难或者不能被移除。考古学证明最早使用失蜡法是在公元前6世纪,首先用蜡制作铸造器物的模型,然后覆盖泥制成外范。当灌入热金属熔液时,蜡熔化并流走(因此而得名);打破外范取出金属器物,外范不能再使用。有明显的证据证明,战国时期青铜器变成了奢华的商品,可以从独立的工场里买到,也不再被王室统治者牢牢控制,可以服务于更广泛的顾客群。例如,在公元前6至5世纪晋国的都城,陕西省南部的侯马发掘出一个青铜铸造遗址,说明在相同的时间段内在同一地点制造了品质各异的器物。[2]制造青铜器的工艺特征表明当时采取了以最大限度增加产量的措施来服务广大的市场,以及采用便捷的方式和重复使用模范图案印模来提高效率。
如果进入流通市场的金属容器在数量上确实有增加,有必要呼吁关注此时期的青铜器;它们必须格外巨大(侯乙墓中最大的一件高126厘米,金属重327.5公斤),或者不得不借助其他手段,诸如镶嵌铜、金、银线或者其他珍贵金属,因为青铜器自身的意义已经经历了转变。现在这种材质的器物不得不与色彩丰富的漆器和丝织品竞争,正如重要遗址中引人注目的陪葬器物。在墓室中发现的被称为鼎的三脚容器,仍然是为了满足祭祀活动的需要,现在是相当地朴素和平淡。而在明确的非宗教活动中使用时,例如宴饮或者陈列,器物就被繁缛地装饰起来。
侯乙青铜器是墓室陪葬品的一部分,因此在1978年发掘之前,它们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使用环境。墓室中这些器物的存在维系了墓室主人生前享受的地位,在死后继续发挥此种功能,由此意义看,两个不同的国度里(地上与地下)存在连续性的身份。尽管上层阶级成员埋葬数量巨大的陪葬品的习俗在中国由来已久,但是上层贵族墓室中的陪葬品在公元前5至前4世纪经历了重要的变化。尤其是屠杀人类或动物仆从去陪伴过世的男主人或女主人的习俗逐渐消失了,这曾经是商代王室大墓葬的特征。侯乙有18位女子陪伴,可能是乐伎,这种情况在他生活的时代已经很罕见。泥或木头摹制的人、动物和器物的形象开始成为替代品。这些变化伴随着上层阶级宗教信仰的改变,并在墓室陪葬品的布局中反映出来。商代王室墓葬,诸如妇好墓,是单室墓,一般很深。另一方面,侯乙墓为死者提供了多间居室,装有门,允许从一个空间进入另一空间,房间中布置的物品仿佛是在现实生活中。现在,墓室是居住空间,为了在下一个千年或更长的时期里一致接受将墓室建造成人生活中居住的空间,增置了代表日常生活中最细枝末节的东西。所做的这些同样是通过图绘、仿制物品或放置物品本身来实现。
但是,在一扇通向身后世界的门前,约公元前500年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对此有非常清晰的想像,长生不死、拥有强大神力的生命居住在那里,他们能在生者与死者之间相互影响。长生不死的生命以动物或类似人的形象显现,重要的是他们不是已故的祖先,而被视为被恳求精神力量的独立之物,因此从这个时代开始他们也变得很重要。他们在墓室中的出现标志着信仰的清晰转变,他们并没有代替对祖先表示尊敬的习俗,相反增加了新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另一个世界和两者之间的神秘性。
在青铜容器上看不到更多的新观念,它们的神圣目的可能助长了设计方面的保守主义。新观念主要体现在全新的工艺形式上,尤其是木漆和丝绸纺织品。简单说来这些被保存下来的器物水平较高,使得它们看起来更重要。我们知道商代宫廷里有丝绸纺织和雕刻、彩漆木制品,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物品看起来是什么样,即便它们和青铜器、玉器共享审美和设计语言(尽管青铜器和象牙杯之间亲近的类似关系使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大)。总的来说,好像我们今天归类为不同的“艺术形式”在受尊重的层次上发生了变化,主要的受益者之一是纺织品。
养殖蚕蛹的技术,拆解、纺纱、编织蚕茧的技术,至少在公元前3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很完善。至于纺织机械,更重要的是重复纺织同一种图案,对于任何审美意识来说纺织机的重要性都不能被过分强调,然而谈及中国最早的纺织品是什么样,因为缺乏证据而留下了推测空间。商和周早期残存的碎片告诉我们,那时的技术已经可以制造相当复杂的自配图案丝织品,人们利用刺绣作为创造更自由的图案设计的手段。也是在最近几年,我们才有大量的来自公元前3世纪的完整丝织品,通过它们开始分析当时丝织品的作用。
证据都来自墓室,因此我们不能依赖它们作为了解上层阶级生活服饰的源头。我们看见的图案可能是专用的丧葬视觉文化的一部分,例如,这是约公元前300年的湖北省马山墓室出土的35件锦衾和锦袍中的一件[图6],(但是也存在这种可能性,是死者生前穿过的外衣改制的寿衣)。马山妇,这位约40岁的无名上层女性自己可能就扮演过巫师,是一位有威力的宗教人士,能够超越现世的王国在灵魂里游走,促成上界与下界的交流。相互交织的虎、龙和凤鸟是这个王国里的动物群,是墓室中的长住者,而不是她日常生活中的代表物。
与青铜器一样,可以合理地假设有专业的纺织工场存在,可能与王室有联系,但是逐渐脱离了他们的直接控制。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些工场是否按性别分隔生产线。已经发现的当时的男性墓室中出土了青铜器但是很少纺织品,而这个女性单人墓中塞满纺织品却未见青铜器,这或许有,也或许没有重大的意义。纺织和刺绣,虽然现在都归类为纺织品,但实际上是两种相去甚远的工艺,清楚的区别之一在于它们与绘画表现的关联性。中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在近代以前纺织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绘画,在马山可能从来就没有为纺织品而做的“设计”。而刺绣与其他表现形式关联的可能性至少出现过,即使没有任何方式暗示绘画在当时的中国是高等级身份的必需品。在缝缀之前,图案可以直接绘制在丝绸上,或者放在薄纱的下面,这足够清楚以导引针线。
You may also be interested in the following product(s)
-

缘分让我们慢慢靠近
£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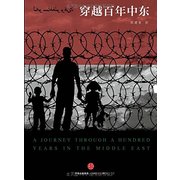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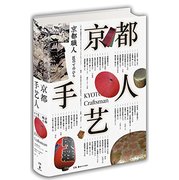




 Facebook
Facebook Twitter
Twitter Pinterest
Pinterest Google +
Goo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