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第1版 (2014年2月1日)
- 外文书名: Shakespeare & Company
- 精装: 268页
- 语种: 简体中文
- 开本: 32
- ISBN: 9787544745277
- 条形码: 9787544745277
- 商品尺寸: 20.8 x 14.8 x 2.4 cm
- 商品重量: 499 g
- 品牌: 江苏译林
Details
基本信息
编辑推荐
这里是乔伊斯的出版社,是海明威的图书室,是菲茨杰拉德的咖啡馆
是艾略特的演讲厅,还是无数流浪作家的通讯地址,这里是书店中的不朽传奇:莎士比亚书店
莎士比亚书店创始人毕奇女士回忆录 亲历二十世纪文坛传奇
恺蒂女士熨帖译笔
万字长文导读 300条专业注释
独家附赠纪念藏书票
收录《尤利西斯》手稿、出版合同及其他珍贵历史影像
名人推荐
一家书店见证及深度参与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与运动,如今是极难想象的,若有,多半也是前朝往事了。因为既要有时代的风云际会,亦要有虔诚于文化的助产士与出类拔萃的作家汇 集一处,而这些,均已风流云散不见踪迹,于是,曾经的莎士比亚书店成为了可供追怀的传奇,源于其别无分号、独此一家。——遆存磊
作者简介
作者 西尔维亚•毕奇(Sylvia Beach)
1887年,于美国巴尔的摩出生
1919年,在巴黎左岸开办英文书店,取名“莎士比亚书店”,遂成英法文学交流中心
1922年,为乔伊斯出版被英美两国列为禁书的《尤利西斯》,声名鹊起
1933年,书店开始多次面临困境,幸而在文化界友人的支持下,仍勉力经营
1941年,受到纳粹威胁,被迫将书店关门,后被投送进集中营。出狱后无心再开书店
1951年,授权乔治•惠特曼再开“莎士比亚书店”,传奇延续
1956年,写下自传《莎士比亚书店》。1962年,于巴黎逝世,享年75岁。
译者 恺蒂
本名郑海瑶,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与伦敦城市大学。自由职业者,现定居伦敦,业余写作,已出版作品集《海天冰谷说书人》,《酿一碗怀旧的酒》,《书缘•情缘》,《书里的风景》,《南非之南》,《聆听南非》,《话说格林》等。译作《我自己的世界:梦之日记》等。
目录
译者序
第一章
“谁是西尔维亚?”
第二章
王府饭店
A.莫尼耶窄小灰暗的书店
第三章
自己的书店
准备开店
莎士比亚书店开张了
第四章
美国来的朝圣者
庞德夫妇
来自花街的两位顾客
舍伍德·安德森
第五章
《尤利西斯》在巴黎
詹姆斯·乔伊斯,由莎士比亚书店转交
第六章
莎士比亚书店前来救援
第戎的达戎提耶
预订者中的缺憾
第七章
瓦莱里·拉尔博
剧院街十二号
希腊蓝和西茜女妖
第八章
乔伊斯的眼睛
在拉尔博家
海绵上的大蒜
乔伊斯和乔治·摩尔
在阿德里安娜书店里的朗读会
“圣女哈里特”
第九章
最好的顾客
第十章
最早的《尤利西斯》
智慧女神密涅瓦——海明威
布卢姆先生的照片
“我的那些涂鸦之作”
莎士比亚书店非常遗憾
第二版
《尤利西斯》定居此地
第十一章
布莱荷
第十二章
杂务
访客和朋友
“圈内人”
第十三章
菲茨杰拉德、尚松和普雷沃斯特
A.麦克莱许
“机械芭蕾”
第十四章
《银船》
惠特曼在巴黎
接触出版社和三山出版社
杰克·坎恩
克罗斯比夫妇
平价出版社
《怪兽》及《大西洋两岸评论》
欧内斯特·沃尔许和《这一区》
《变迁》
《交流》
我们的朋友斯图尔特·吉尔伯特
第十五章
儒勒·罗曼和“伙伴们”
一个法国的莎翁迷
让·施隆伯杰
莱昂—保尔·法尔格
雷蒙德
第十六章
“我们亲爱的纪德”
我的朋友保尔·瓦莱里
第十七章
乔伊斯的《流亡者》
“A.L.P.”
两张唱片
第十八章
《一诗一便士》
《我们
海盗版
第十九章
《尤利西斯》的后继者
詹姆斯和两个约翰
第二十章
去远方
乔伊斯的生活方式
第二十一章
《尤利西斯》去美国
三十年代
莎士比亚书店之友
“一九三七年博览会”
第二十二章
战争和沦陷
莎士比亚书店消失了
第二十三章
解放
海明威解放剧院街
译后
附录
序言
毕奇与莎士比亚书店
(译者序)
(一)
一九六四年,海明威的回忆录《流动的盛宴》出版,回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文艺圈。书中对许多在巴黎活动的作家颇有不逊之词,但有一段描写却充满了赞扬:“西尔维亚有一张生动的,如同雕塑般轮廓清晰的脸,她褐色的眼睛如同小动物般充满活力,又如同小女孩般充满快乐。她的波浪般的褐色头发往后梳,露出她漂亮的前额,在耳朵下剪短,与她褐色的天鹅绒外套的衣领相平。她的两条腿很漂亮,她善良,愉快,非常有趣。她很喜欢开玩笑,也喜欢八卦,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没有人比她对我更好。”
被描写的是西尔维亚•毕奇,《流动的盛宴》出版时,毕奇已去世两年。在毕奇之前几年出版的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中,她对海明威也有许多同样温馨的回忆和由衷的赞扬。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一年间,毕奇的莎士比亚书店是大洋两岸英语法语作家的聚集地,这里既是书店,也是图书馆,一批又一批的作家到这里来买书、借书、会朋友、聊天、喝咖啡、谈心事。庞德、乔伊斯、海明威、斯坦因、菲茨杰拉德、拉尔博、罗伯特•麦卡蒙、多斯•帕索斯、桑顿•怀尔德、曼•雷、茱娜•伯恩斯、尚松、普雷沃斯特、麦克利什、莱昂—保尔•法尔格、纪德、布莱荷、保尔•瓦莱里、乔治•安太尔、亨利•米勒、托马斯•伍尔夫等等。莎士比亚书店是自我流放的作家们在巴黎的家,是他们收取信件的稳定的通讯地址,是他们的“左岸银行”和“邮政总局”。
毕奇是一位古怪的书商兼图书管理员。她的图书馆毫无系统,她要出售的书上从无价码,她更没有任何营销活动。而且,她与她要卖出的每一本书都难舍难分。但她是位好书商,因为她知道不同的读者需要不同的书,她曾形容她的工作,说向读者推荐书,就像是鞋店老板为顾客找鞋子一样,非得合脚才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莎士比亚书店》新版中,有美国诗人、出版家詹姆斯•拉何林(JamesLaughlin)写的序言,其中一段描写了毕奇的书店:
和现在的许多书商不同的是,西尔维亚鼓励顾客们在书店里随便读书。对她来说,莎士比亚书店不只是一个生意,它更是一个事业,是为最好的文学作品服务的事业。她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就博览群书,阅读极广,她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她的文学品位。为了鼓励大家随意阅读,她还特地到跳蚤市场上去买了好几把巨大古老的扶手椅回来,我还能记得,这些椅子坐上去非常舒服。所有的书架都是靠墙摆着的,书店的中间部分是开放式的,就像一间起居室一样,明亮的光线能通过窗子照进来。你一走进商店,目光马上就会被两面墙的书架之上挂着的作家们的照片吸引住,最重要的位置上挂着惠特曼、爱伦•坡和王尔德(还有两张非常精美的布莱克的素描),其他还有当时所有一流作家的照片——乔伊斯,庞德,劳伦斯,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等等。书店里的一个支架上,摆放着当时最出色的评论杂志:《小评论》、《扫帚》、《日晷》、《这一区》、《千册诗评》、《自我主义者》、《新英文评论》,当然还有尤金•约拉斯和他的同仁们“语言革命”的阵地《变迁》。一九三六年,我的新方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年鉴就是题献给“语言革命”的。因为冬天没有暖气,所以,在书店中还有一个炉子。在旁边有一个小房间,需要时,西尔维亚或哪位没有地方住的作家可以在那里过夜。
对于毕奇,拉何林的印象是:
西尔维亚虽然长得像小鸟一样灵巧,但她却如一匹良种赛马那样充满力度和能量。她抽烟很厉害,总是不停地在忙这忙那。我还记得她在书店中,不管做什么,动作都是那么迅捷。我也记得她的眼睛非常明亮,她很有幽默感(特别喜欢用双关语),无论别人说什么,她总能妙语答对。在莎士比亚书店中,从来不会有一刻让人觉得无聊。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聚集在巴黎的美国作家们,大多是愤世嫉俗的“迷惘的一代”,他们实验新的写作方法,试图打破传统常规。与这些叛逆的作家们相比,毕奇就显得很循规蹈矩。出版史家休•福特(HughFord)在一篇题为《毕奇:从普林斯顿到巴黎》(FromPrincetontoParis:SylviaBeach)的论文中说,她给人的印象是“自我控制”、“脚踏实地”、“端庄整洁”、“可敬可畏”,她更喜欢穿男装:“精心剪裁的天鹅绒外套,低开的白领子上的蝶形领结,一顶小毡帽,一件没有什么特色的深色布料做成的衬衫,一双舒服的美国皮鞋”,“她的头发被卷成整齐的小波浪,她的视力一直非常糟糕”,“她戴着一副钢质框架的眼镜,让她看上去稍稍有些严厉”。但正是她和她的书店的稳定性让她成为一块吸铁石,一个中心,来来往往的作家们星转斗移,划过巴黎的夜空,消失在远处,但过了不久,可能又会飞驰回来,出现在莎士比亚书店里。
毕奇一九一七年到巴黎定居,两年后创立莎士比亚书店,她在巴黎一直住到七十五岁去世,巴黎是她的第二故乡。二战前在巴黎有两个著名的美国女人,一个是毕奇,另一个是斯坦因。斯坦因曾说:“美国是我的祖国,但巴黎是我的家”,此话也许形容毕奇更确切,因为斯坦因毕竟只是巴黎的一位过客。毕奇的法语比斯坦因的要好很多,瓦莱里曾说自己最喜欢毕奇能“以完全美国的方式说出最有把握的法国成语”,这让“她作出的每一句评论都有警句和寓言的深度与力量”。
毕奇是谦卑的,这让那些自傲的作家们感觉到舒服安全。毕奇也是以谦卑恭敬的态度对待巴黎。我喜欢英国女作家布莱荷所描述的毕奇:“她热爱法国,她让我们觉得住在巴黎是一种特权,但她没犯那种常见的错误,她从未试图与这个异域土地有太亲近的认同,因为她毕竟没有在这里的童年记忆。她能将伟人和俗人混在一起,她能让大家密切相连的纽带是因为我们都是艺术家、探索者。我们会改变,城市也会变化,但是,在离开这个城市一段时间后再回来,我们总能看到西尔维亚在等着我们,怀里捧满了新书,在她身边的角落里,往往还站着一位我们正想要见到的作家。”
(二)
当然,让莎士比亚书店不朽的,是因它曾是《尤利西斯》的出版商。毕奇的回忆录中写道:“我等在站台上,我的心就像火车头一样怦怦直跳。我看着第戎来的火车慢慢停下来,我看见火车司机下了车,他的手上拿着一包东西,东张西望地寻找着,他在找我!几分钟后,我就敲开了乔伊斯家的门,把第一本《尤利西斯》交到他们的手上,那天正好是一九二二年二月二日。”那天正是乔伊斯四十岁的生日,此书的出版,当然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一九二〇年夏天,毕奇与乔伊斯在朋友家相遇,乔伊斯一家刚刚搬到巴黎。毕奇崇拜乔伊斯,在回忆录中写道她第一次与乔伊斯握手:“我们握了握手,更确切地说,他把他软绵绵,没有骨头的手放进我的硬邦邦的小爪子里……”第二天,乔伊斯顺着小街走向莎士比亚书店,那个镜头是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定格:“乔伊斯就顺着我书店前窄窄的上坡路走来,他穿着深蓝色的斜纹哔叽布料西装,头上朝后戴着顶黑色的毡帽,在他窄窄的双脚上,是一双并不太白的运动鞋。他的手上转动着一根手杖”,“乔伊斯的衣着总是有些寒酸,但是他的神态是如此高雅,他的举止是那么出众,所以,人们很少会注意到他究竟穿着什么。”
乔伊斯抱怨没人出版《尤利西斯》,毕奇毛遂自荐,担当起出版此书的重任。回忆录中将出版《尤利西斯》的前前后后交待得非常详细:第戎的印刷厂,希腊蓝的封面,催促乔伊斯完成修改稿,发动在巴黎的作家们兜售《尤利西斯》预订单,走私进入美国等等。后来有不少人批评毕奇不够专业,说她出版的《尤利西斯》中错误百出。确实,乔伊斯的手书难以辨认,而且他又对原稿不停修改,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后来添加的,而且初版时,因为要赶时间,共有二十六位压根就不懂英文的排字工人对此书进行排版,所以,第一版《尤利西斯》中大约有两千多个错误。以后的各个版本中,错误依然很多,修改了前版的错误,又增加了新的错误。最近,在伦敦“名作展”中一位善本书商处,见到一本当年售价一百五十法郎的纸印本《尤利西斯》,蓝色封面大开本雍容大方,书商的要价将近三十万英镑。
毕奇不仅是乔伊斯的出版商,更是他的助理、秘书、银行、邮局。乔家大事小事都要找她,她简直就是乔伊斯一直拄着的一根拐棍。即使她出门在外,乔伊斯也不放过她,他们之间的许多通信,大多数都是毕奇夏天在山中度假或旅行在外时所写。乔伊斯总是要求毕奇最晚第二天就必须回信,信必须特快寄出,或由送信的邮差直接带回。而且,乔伊斯花钱大手大脚,常常入不敷出,莎士比亚书店就像是他家的钱口袋。
在《尤利西斯》初版后的十年中,莎士比亚书店将此书重印过十一次。文坛对它的兴趣和热情不减,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本书赚了不少钱,乔伊斯的夫人诺拉和他儿子更这么认为,他们屡屡给乔伊斯施加压力,让他去叫毕奇把账算清楚,到底有多少利润。
对于乔伊斯的这位夫人,毕奇下笔相当客气。一方面,她写道诺拉“整天责骂她的孩子们和她的丈夫,说他们偷懒无能”,而且,她“是个不愿和书发生任何关系的女人”,对《尤利西斯》,“她连翻都懒得翻开”,她还曾告诉毕奇她“后悔自己没有嫁给一个农夫或银行家,甚至是一个捡破烂的”,而是嫁给了一个“可鄙”的作家。从毕奇的描述来看,乔伊斯的婚姻肯定不幸极了,但毕奇却能打圆场,说“乔伊斯喜欢被诺拉叫成是窝囊废,因为他在别处一直受人尊敬,所以这种谩骂反而是一种调剂”,还说,“他和诺拉的婚姻是他这一生中最幸运的一件事。在我所知道的作家的婚姻中,他们的婚姻可以说是最幸福的”。这样的断语让人怀疑毕奇是否在用反讽。但是,毕奇有一点是对的:“我能理解诺拉根本就没有必要去阅读《尤利西斯》,难道她不正是这本书的灵感来源么?”
但是,在出版《尤利西斯》究竟花了多少赚了多少上,莎士比亚书店确实只有一笔糊涂账,所以,这也是以后乔伊斯与毕奇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为此,阿德里安娜一直想把毕奇从乔伊斯身边拖开,一九三一年五月,她写了一封很愤怒的信给乔伊斯,因为纪德曾经说过乔伊斯对名和利漠不关心,简直是圣人,所以,阿德里安娜在信中说:“有一点纪德并不知道——就像我们要在诺亚的儿子身上盖一块遮羞布一样——正相反,其实你对金钱和成功都非常在乎!”信的最后,阿德里安娜也道出她们的苦衷:“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困难,但是更困难的还在后面呢,我们现在只能坐三等席了,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只能骑着棍子出门。”这封信虽然让乔伊斯很受伤害,但是他没有和阿德里安娜开战。但是他与毕奇的关系没有再恢复过。
毕奇在回忆录中所描述的乔伊斯彬彬有礼、对人和蔼可亲,他是她心目中的英雄。毕奇虽没太多抱怨,但后期的字里行间能看出她的委屈:“人们可能会觉得我从《尤利西斯》中赚了不少钱,其实,乔伊斯的口袋里肯定装了一块吸铁石,所有赚到的钱都被吸到他那个方向去了”,“当然,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和乔伊斯一起工作,为乔伊斯工作,所有的乐趣都是我的——确实也是其乐无穷——而所有的利润都是他的。”
美国作家、评论家马尔克姆•考利曾说:“乔伊斯接受别人给他的好处,或是要求别人替他做什么时,仿佛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神圣的使命。他好像是在说,能够献身给他,那可是一种特权,谁帮他还了债,以后是能在天堂里得到报酬的。”T.S.艾略特后来回忆说,乔伊斯去英国看望他时,他惊奇地发现乔伊斯竟然没有银行账户,“他需要钱花时,就写信给西尔维亚,她会很快给他寄一张银行汇票来,然后他就可以到我的银行里把它兑换成现金。”
拉何林在他的新版序言中说他对毕奇与乔伊斯的关系没有资格多做评论,但他觉得在《尤利西斯》出版那天,乔伊斯仿照《维罗纳二绅士》中的诗句写的那首感谢西尔维亚的打油诗“不痛不痒”、“有气无力”,“想想他那一年给人带来的种种麻烦,他应该多花些心思来写首感谢诗吧。但是这位被庞德称为‘耶稣詹姆斯’的乔伊斯是很少会认识到别人给他带来的好处,只有对他的大恩主哈里特•韦弗除外。随手翻翻庞德—乔伊斯的那本通信集,就能从至少几十封庞德的信件中,看到埃兹拉如何想方设法运用各种关系帮助穷途潦倒的乔伊斯,帮他寻找出版社,寻找赞助人,甚至帮他去取衣服,为他的眼疾寻找药方,但是,在乔伊斯的信中,我们看不到一句对庞德的劳碌表示兴趣的话。”
一九三二年初,乔伊斯通过家中亲戚与兰登书屋联系,兰登书屋有意出版《尤利西斯》,但必须要毕奇放弃其版权。乔伊斯没有亲自出面对毕奇提出要求,但有不少他的说客来劝毕奇为“伟人”考虑,把乔伊斯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毕奇别无选择,只得无偿放弃。同年三月,乔伊斯和兰登书屋签约。
毕奇回忆录出版时有不少删节部分。关于放弃《尤利西斯》版权一事,原稿中有一段这样评论乔伊斯:“这以后,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他不仅仅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作家,他也是一位相当精明的生意人,手腕非常强硬。”并称他为“虽然讨人喜欢,但也相当残忍”。在当时给姐姐霍莉的信中,毕奇抱怨:“他就像拿破仑一样,觉得其他人都是为他服务而存在的,他可以把他们的骨头磨成面粉,做成他的面包。”但在最后出版的《莎士比亚书店》中,毕奇只这样写道:“至于我个人的情感,我并不以此为荣,而且现在我怎么想都无所谓了,我也就应该及时将这样的情感抛开。”
(三)
《莎士比亚书店》虽是毕奇的回忆录,但书中几乎没怎么谈到她的个人情感。当然,毕奇和她的伴侣阿德里安娜的关系随处可见。阿德里安娜自己的书店和她出版的文学杂志是当时法国文坛的一部分,她也一直是毕奇的顾问和坚强的后盾。但是,毕奇对她们的关系不愿张扬,在一段删节的文字中,毕奇这样写道:
我想那个夏天,当纪德来耶荷镇与我和阿德里安娜一起度假时,我们之间什么奇怪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可能让纪德很失望。一位认识我那令人尊敬的父亲且每周都要去美国教堂的女士曾告诉别人,她知道我的书店中尽是些见不得人的事,她压根就不会到我的店里来。我的“爱情”,不管怎么列单子,可能都是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乔伊斯和莎士比亚书店。仅仅有一次,麦卡蒙如此吸引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的感情……当我还是个少女时,有一次我母亲告诉我“千万别让男人碰你”,从肉体上来说,我总是很害怕男人,也许这是为什么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幸福地和阿德里安娜生活在一起。
有关她对麦卡蒙的那段感情,毕奇在另一段删节掉的回忆录中写道: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深深地被麦卡蒙吸引着,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也爱上了他,甚至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的感情。当时我正在海边度假,可能是因为无所事事的原因吧。他没有回信,等到两周后我回到巴黎时,发现我已经完全摆脱了那份情感,我如释重负。后来,麦卡蒙来到我的书店时,我看到他的神情非常焦虑不安,我就告诉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害怕了。不用什么打击,我的风流韵事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毕奇是一位奇女子,最后,我要引用法国作家尚松对毕奇的评论:
西尔维亚就像是一只传播花粉的蜜蜂,她让各方来的不同的作家进行交流,她将英国、美国、爱尔兰和法国的作家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功效要远远胜过四国大使。乔伊斯,艾略特,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布莱荷,还有其他的许多作家们,大家都来到这个坐落在巴黎市中心的莎士比亚书店,来这里和法国作家们见面,并不纯粹是因为友谊的乐趣,而是要通过对话、阅读和接触进行交流,这种交流真是很神秘,就像我自己,我所受到的菲茨杰拉德的影响……还有其他作家互相之间的影响,这都是西尔维亚的秘密所在。
二战开始,巴黎被德军占领,许多人劝毕奇离开,她没有,她的书店仍然照常营业。但在一九四一年,一位德国军官走进她的书店,看到一本陈列在橱窗里的《芬尼根守灵夜》,想要购买,被毕奇拒绝。军官恐吓毕奇说要把她店中的东西全部没收。于是,毕奇就和朋友们一起,仅仅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将店中的所有东西搬到了楼上的一间公寓里,并将店名粉刷得无影无踪。就这样,毕奇的莎士比亚书店消失了。
一九六四年,为了对毕奇表示敬意,美国人乔治•惠特曼将他开在巴黎圣母院旁塞纳河左岸的英文书店易名为“莎士比亚书店”,至今,这家书店仍是巴黎的文学地标之一,是许多文学青年和游客要去朝拜的地方。
恺蒂
2013年12月3日
后记
译 后
又来到塞纳河左岸巴黎圣母院旁边的那个绿色门面的书屋,莎士比亚书店。每次来巴黎总要到这里来买一本书。
第一次来到这家书店,是二十年前,那时,当堂而坐的是八十岁的老人乔治•惠特曼。他穿着色彩并不搭配的背心和外套,一头白发上有火烧的痕迹。据说他很少去理发馆,头发长了就用蜡烛烧掉,说这种剃头法又快又省钱。记忆中书店中的顾客并不多,所以,当时我还与老人聊了会天。他问我是否要咖啡,又问我是否有住处,接着就兴冲冲地告诉我他和中国还有一段缘分,幼年时曾随父亲住在南京,曾坐蒸汽火车去上海,曾在苏州见过一位天下最美的姑娘,又说起那之前五年,他重返中国,想在南京开一家英文书店,但没能成功,只余遗憾。他还告诉我他是美国大诗人惠特曼的孙子,他心中的女英雄是西尔维亚•毕奇,而毕奇心中的英雄则是他爷爷,毕奇曾经收藏过他爷爷的手稿,还举办过一个惠特曼的展览。当时我竟相信了,后来读到有关他的文章,才知道这是他经常爱说的一个“传奇”,他的父亲确实叫沃尔特•惠特曼,是一位外科医生,只是与大诗人同名而已。那次从书店中买了一本书,就是毕奇的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可惜,这二十年来无数次搬家,这本书已经找不到了。
惠特曼二战之后来到巴黎,一九五一年在目前地址上开了一家英文书店兼图书馆,继承的完全是原莎士比亚书店的精神。与毕奇相比,惠特曼的性格更为古怪,他把自己的小店称为“假装成书店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共和国”,一个波希米亚的庇护所。他的书店也是旅行者的邮政总局、免费咖啡馆,而且,较毕奇更进一步,他在书店里增加了更多的横七竖八的床位,可以让多位付不起旅店费用的文学青年在这里过夜,这些住客们可以在书店中帮忙,惠特曼对他们的唯一要求是每天必须读一本书,当然,也有人滥用惠特曼的好客热情,据说曾有一位英国诗人在这里一住就是七年。
惠特曼的书店名气渐响,也吸引了一批作家,贝克特、亨利•米勒、劳伦斯•杜威尔、布莱希特、阿瑟•米勒、克鲁亚克、金斯堡等等,或在这里住过,或来这里朗读过作品。艾纳伊丝•宁曾将她的遗嘱留在这里,以日记著称的她在五十年代的巴黎日记中,曾这样描绘惠特曼的书店:“在塞纳河畔有这么家书店,一栋画家郁特里罗笔下的房子,地基不是很结实,小小的窗户,起皱的百叶窗。还有乔治•惠特曼,营养不良,留着胡子,如同他的书堆中的一位圣人,借书出去,让身无分文的朋友住在楼上,并不急于卖书。在书店最里面,是一个窄小拥挤的房间,一张小桌子,一个炉子。那些为书而来的人不停地说话聊天,乔治则试图写信,拆开邮件,预定书籍。一个小小的让人不能相信的楼梯通到楼上,通向他的卧室,或公共卧室,亨利•米勒和其他的来访者们,会在那里住下。”
惠特曼的书店开张时,西尔维亚•毕奇仍住在巴黎。二战中,因不愿将一本《芬尼根守灵夜》卖给一位德国军官,她索性将书店清空关门,战后她无意再重振旗鼓。惠特曼的书店也是她常常光顾的地方,来这里借书买书,与其他作家见面。有这么位疯狂的美国人在这个城市里全面继承了她当年的精神,她应该是欣喜的。所以,她去世前,在一次杜威尔的朗读会上,她同意让惠特曼沿用“莎士比亚书店”这个名字。于是,惠特曼的书店,就名副其实地成了战前莎士比亚书店的继承人。
如同毫无经济头脑的毕奇,惠特曼的财务也是一笔糊涂账。时代发展,全球都在数据化、电脑化,他掌管的书店一直没有任何现代化设施,没有信用卡收款机,架上的书也杂乱无章,没有任何检索系统,店中的书和钱也常常消失,惠特曼总是耸肩以对,不加追究。他的书店如何维持下来,他又如何通过法国税务局对书店的几次查账,这一直是个谜。
二〇一一年,惠特曼老人去世,享年九十八岁。现在,书店由他的女儿掌管(芳名就叫西尔维亚•毕奇•惠特曼)。她是惠特曼唯一的孩子,出生在巴黎,母亲是英国人,她记得她的童年“如同生活在一种童话里,赤脚在书店中走过那些睡着人的床”。但七岁时父母离异,她跟妈妈回到英国,在那里长大。二十一岁时,她来到书店帮助父亲,原本只计划待一个夏天,没想到就没有再离开过。在她的管理下,书店风格依旧,室内装饰也没有改变,书架间的床和沙发等仍在,但比以前干净许多,床单不再油光发亮,沙发也不再露着海绵。她努力要让书店走进二十一世纪,在店里安装了电话、电脑和信用卡付款机。她也建立了书店网站,并把每次在书店中留宿的人数限制到六位。书店还每年举办文学节,并邀请作家到书店签售朗读与读者见面。
现在,亚马逊等网上书店们冲击实体书店,实体书店究竟能维持多久,一直是大家讨论的问题。然而,从财务的角度来说,无论在毕奇还是在惠特曼手下,莎士比亚书店一直就算不上是成功的“生意”,仅仅是维持而已。它之所以会成为巴黎的文化地标,更因为它是英语文学与法语文学之间文化交融的纽带。
希望年轻的西尔维亚•毕奇•惠特曼能有足够的功力,将莎士比亚书店的这一传统继承下去。
最后,要感谢译林出版社的张远帆几年前在苏浙汇的饭桌上说服我翻译这本《莎士比亚书店》,翻译的过程也是对那个趣味无穷的年代的研究,所以,也就拉杂加了许多注释。
恺蒂
2013年11月28日
文摘
第五章
《尤利西斯》在巴黎
我第一次遇到乔伊斯,是在一九二〇年夏天,那是我的书店开张营业的第一年。
那是一个闷热的星期天的下午,阿德里安娜要去诗人安德烈•史毕尔(Andre Spire)(注释42)家参加一个聚会,她一定要我陪她同去,她向我保证说史毕尔见到我会非常高兴,但是我还是不想去,因为我虽然很崇拜史毕尔的诗歌,但是我并不认识他本人。但是一如往常,阿德里安娜还是赢了,我们一起前往奈伊里镇(Neuilly),当时史毕尔夫妇住在那个小镇上。他们住在布隆涅森林街(rue du Bois de Boulogne)三十四号那栋房子二楼的公寓里,我还能记得那周围如荫的绿树。史毕尔长得有些像诗人布莱克,留着部《圣经》时代的大胡子和浓密的头发,他热诚地和我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打招呼,并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对我耳语道: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也来了。”
我非常崇拜詹姆斯•乔伊斯,他也在场的消息太出乎我的意料,我害怕得几乎要立即逃走。但是史毕尔告诉我说是庞德夫妇把乔伊斯夫妇带来的,我能从开着的门中看到埃兹拉,我和庞德夫妇认识,所以,就进了屋。
埃兹拉果然在里面,四肢伸展着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我后来曾为《信使文学期刊》(Mercure de France)写过一篇文章,说庞德那天穿着件蓝色衬衫,正能配上他的蓝眼睛,但是庞德立即给我写了回信,说他的眼睛根本就不是蓝色的,所以,在此我要把蓝眼睛的那句话给收回。
我看见了庞德夫人,就上前去和她说话。她正在和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年轻女人聊天,她向我介绍说这是乔伊斯夫人,然后她就走开了,留下我们俩自己说话。
乔伊斯夫人身材高挑,不胖也不瘦。她很有魅力,红色的鬈发配着红色的眼睫毛,双目炯炯有神,她的爱尔兰口音抑扬顿挫,还有一种爱尔兰人特有的高贵。我们能用英文交谈,这让她很高兴,因为对于别人的法语谈话,她一句话都听不懂。如果大家都讲意大利语,那就不一样了,乔伊斯一家曾经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住过,他们都会说意大利语,甚至有时在家里也用意大利语交流。
我们的交谈被史毕尔给打断了,他来邀请我们在一张长长的餐桌前入座,那天的晚餐是美味的冷菜。我们边吃边喝,我注意到其中一位客人滴酒未沾。史毕尔多次试图往他的酒杯里斟酒,但是都被拒绝了,最后,他索性把酒杯给倒过来放在桌子上,这也就省去了所有的麻烦。这个客人就是詹姆斯•乔伊斯。后来,庞德把所有的酒瓶子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一字摆开,这让他的脸涨得通红。(注释43)
晚餐之后,阿德里安娜和哲学家朱利安 •班达(Julien Benda)(注释44)开始讨论班达最近发表的关于当代最顶尖的几位作家的评论,他们的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人,大家手上端着咖啡杯,有兴趣地倾听着他们的讨论。受到班达直接攻击的作家有瓦莱里、纪德、克洛岱尔,还有一些其他人。
我将阿德里安娜留在那里,让她为她的朋友们辩护,我来到一个小房间里,这里的书籍堆到了天花板,窝在角落里的两个书
架之间的,是乔伊斯。
我用颤抖的声音问:“您就是伟大的詹姆斯•乔伊斯么?”
“对,我是詹姆斯•乔伊斯。”他回答。
我们握了握手,更确切地说,他把他软绵绵,没有骨头的手放进我的硬邦邦的小爪子里边——如果你也能称之为握手的话。
他中等身材,很瘦,有些驼背,但是举止优雅。他的手很引人注目,它们很窄,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上,戴着镶在厚厚的底座上的宝石戒指。他的眼睛是深蓝色的,非常漂亮,闪着天才特有的光芒。我也注意到他的右眼睛看上去有点不正常,右边的眼镜片比左边的稍厚些。他的头发很浓密,深褐色,卷曲着,额头上的发际线很高,头发从发际线往后梳,盖过高高的头颅骨。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他看上去最为敏感。他的皮肤很白,有些雀斑,而且泛着红晕。他的下巴上留着山羊胡子,他的鼻子的形状很好,嘴唇很薄而且线条分明,我想,他年轻时肯定是一个很帅的小伙子。
乔伊斯的声音很甜美,音质如同一位男高音,让人陶醉。他的吐字非常清晰,有些字的发音完全是爱尔兰口音,例如 “书籍”(book)、“看”(look)以及一些以th开头的字,而且他的声音也是爱尔兰人独有的,除了这些以外,简直听不出他的英语和其他英国人的有什么区别。他用很简单的语言表达自己,但是他选择的词语以及这些词语的发音都非常讲究。这当然一部分是因为他对语言的热爱和他的乐感,但我也觉得这可能还和他多年教授英语有关。
乔伊斯告诉我他最近才来到巴黎,庞德建议他把全家搬到这里,也是通过庞德,乔伊斯认识了路德米拉•萨文斯基女士,她让乔伊斯一家在她帕塞区的公寓里住几个星期,这样他们能有时间找一个稳定的住所。萨文斯基女士是乔伊斯在巴黎的最早的朋友之一,而且她还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翻译成法语,法语的书名是《达德勒斯》。乔伊斯的另一位在巴黎的较早的朋友是珍妮•布拉德利夫人,她翻译了《流亡者》。
“你做什么的呢? ”乔伊斯问。我向他介绍了我的莎士比亚书店。我的名字和我书店的名字,都让他觉得很有趣,他的嘴角浮起一丝迷人的微笑。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小笔记本,记下了我的名字和地址,他写字的时候把笔记本凑得离眼睛很近,这让我顿生一种伤感。他说他会来看我。
突然,外面传来一阵狗叫声,乔伊斯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苍白,他的全身在发抖。狗叫声是从路对面传来的,透过窗子,我看见一条狗在追一只球。它虽然叫声响亮,但在我看来,很明显它并没有要咬人的意图。
“它会进来么?它很凶么?”乔伊斯问我,他心神不安(他的“凶”这个字的发音很长)。我向他保证说狗肯定不会进来,而且,那条狗看上去一点都不凶。但是,他还是非常担心,每一声狗叫都让他害怕。他说他从五岁开始就一直很怕狗,因为“这种动物” 曾在他下巴上咬过一口,他指着他的山羊胡子说,留这样的胡子就是为了掩盖那个伤疤。
我们继续交谈,乔伊斯的言谈举止都非常简单,我知道在我面前的是当代最伟大的作家,这让我激动,但同时,我也觉得在他面前很放松。那次以后,虽然我一直意识到他是位天才,但是,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别人比他更容易交谈。
这时,客人们都开始告辞了,阿德里安娜找到了我,我们一起去和史毕尔夫妇告别。我感谢史毕尔先生的盛情款待,他说希望我没有觉得太无聊。怎么可能无聊?我遇见了詹姆斯•乔伊斯。
注释:
42. 安德烈•史毕尔(1868—1966),法国诗人、作家、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
43. 后来,在他们熟悉之后,乔伊斯告诉毕奇他只是在晚上八点钟之前滴酒不沾。
44. 朱利安•班达(1867—1956),法国哲学家、小说家。
You may also be interested in the following product(s)
-

荣宝斋画谱125:梅竹部分
£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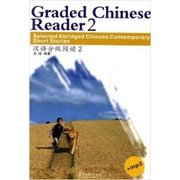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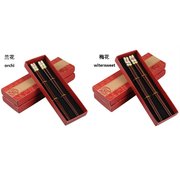



 Facebook
Facebook Twitter
Twitter Pinterest
Pinterest Google +
Google +